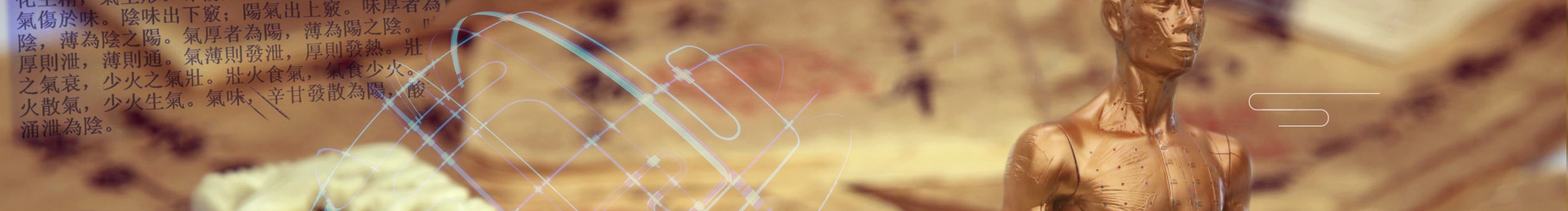《寒温条辨》 註家註释 卷一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天以阴阳而运六气,须知有大运,有小运,小则逐岁而更,大则六十年而易,大小有不合。大运于阳,岁位居阴,是阳中之阴,犹夏日之亥子时也;大运于阴,岁位居阳,是阴中之阳,犹冬日之巳午刻也。民病之应乎运气,在大不在小,不可拘小运,遗其本而专事其末也。譬之子平1,以运为主,流年利钝,安能移其大局乎?病而与大小俱合无论矣。有于大运则合岁气相违者,自从其大而畧变其间也,此常理也。有于小则合,于大相违,更有于大运岁气俱违者,偶尔之变,亦当因其变而变应之。如冬温夏凉,怪病百出,俱不可以常理论也。总以大运为主,不以岁气纷更,强合乎证。又不设成见于中,惟证为的,与司天不合而自合,庶乎其近道矣。若概谓「必先岁气,毋伐天和」,似非世则之言。尝稽东垣李氏,一以补中为主;丹溪朱氏,一以滋阴为重;戴人张氏,一以荡涤为先,皆能表表于世。总得挈领提纲,故合一本万殊之妙。否则当年岂无岁气,而必各取其一耶?再以痘疹言之,有抱要于保元,有独取于辛温,有得意于清泻,是亦治痘之名手,何不见有逐年之分別耶?要知大运之使然,非三氏之偏僻也。如曰偏僻,则当年各操其一以应世,何以得各擅其胜乎?后学不明其故,各效其一而不通变。亦有畏其偏僻,而第据证按时,侈谈岁气,以示高卓,皆不知循环之大运者也。馀留心此道,年近四旬,乡闱已经七困,肇于干隆九年甲子,犹及谢事。寒水大运,证多阴寒,治多温补,纵有毒火之证,亦属强驽之末。自兹已后,而阳火之证渐渐多矣,向温补宜重者变而从轻,清泻宜轻者变而从重。迨及甲戌乙亥,所宜重泻者,虽极清极解而亦弗騐矣,势必盪涤而元枭之势始杀。至甲申乙酉,盪涤之法向施于初病者,多有首尾而难免者矣。歷年已来,居然成一定局。间有温补者,什一千百而已,是大运转于相火矣。凡时行之气,如正伤寒与冬温、风温、暑温、溼温、秋温、飧泻、痎疟、燥咳、吐痢、霍乱,并男妇小儿一切诸证及痘疹,民病火病十八九。何况温病从无阴证,得天地疵疠旱潦之气,其流毒更甚于六淫,又岂寒水司大运者之所可同年语哉?自古运气靡常,纯驳无定,病故变态靡常,补泻无定。今之非昔,可知后之非今,先圣后圣其揆一也,易地则皆然矣。任胸臆者,断断不能彷彿。馀于当事,时怀冰兢,惟恐偏僻致误,庶几屡经屡騐,差可自信,亦有莫挽者,明知其逆不必治,不过热肠所迫耳。 |
天以阴阳用以运转六气,必须知道有大运与小运,小运是每年更换一次,大运是六十年更换一次,大运与小运之间是有所不相合者。大运在阳而岁位于阴,是阳中之阴,就像夏天晚上九时至凌晨一时;大运在阴而岁位于阳,是阴中之阳,就像冬天上午九时至下午一时。百姓之疾病与运气相应,主要在于大运而非小运,不可以拘泥于小运,遗忘其根本而只专注于支节。就像命理学中以运气为主,而当年运气之有利或不利,又怎样能影响其命理之大局呢?如果发生疾病而与大运及小运均符合,就不用再说了。但有的是与大运相合而与岁气则相违,自当从乎其大运而稍微就岁气作些变通,这是常理。有的与小运相合,与大运则相违,更有的与大运及岁气均相违,偶尔之变化,亦当因应这些变化而有不同之认识。例如冬天温暖,夏天凉快,出现了各种奇怪之疾病,这些都不可以用常理推论。总之以大运为主,而不应以岁气之纷纭变更而将其勉强与病人之证候进行对应。又不应心中先有成见,只有以证候为中心,即使与司天之气不合亦会自然相合,这或许是最接近天道了。如果一概认为「必先岁气,勿伐天和」,则不是当世必须遵循之原则。曾经作过考证,李东垣以补益中土为主,朱丹溪则重视滋阴,张戴人则全以荡涤攻邪,而他们全部都能够成为有卓越贡献之医家。他们都能抓住事物之重点,所以都能合符万变不离其宗之精妙。否则,当年怎么会沒有岁气,而必须只能从中各取其一呢?再以痘疹为例,有医者执着于保元之法,有医者独取于辛温之法,有医者以清泻之法自豪,他们都是治痘疹有名的医者,为何不见每年会有所不同?关键要知道这是大运所致之结果,而不是三位医家各有其一家之言。如果说是只是一家之言,为何当年各自只用其一法以应对各种疾病,便能展现其各自治病取效之优势呢?后学不明当中之理,只能各自效法其中一个医家而不知通变。亦有医者畏惧他们只是一家之言,而只能引经据典,泛泛讨论岁气以显示其高明,他们都不知道大运是不断循环的。我留心于此道,差不多四十多年,经过七次乡试均落选,由干隆九年甲子开始,等到放弃考科举时。该年大运是寒水,证候多见阴寒,治法多以温补,纵然有火毒之证,都属于强弩之末。自此之后,阳火之证渐渐多了,通常宜以温补为重者变得少了,而以清泻为轻者则变得多了。等到甲戌乙亥这些年,应当重用泻下者,哪怕重用清解之法都不会有效,势必要将病邪从根泻尽才能除去邪气。到了甲申乙酉这些年,一向在病初时就运用之荡涤之法,在整个疾病过程中亦都难免要用。这么多年以来,基本已成定局。间中有需要用温补者,只是极少数了,是因为大运转而为相火了。凡时行之气,如正伤寒病与冬温、风温、暑温、湿温、秋温、飧泻、痎疟、燥咳、吐痢、霍乱,以及男科、妇科、小儿一切诸证及痘疹,百姓之病属火热者十有八九。更何况温病从来沒有阴证,是由天地间疵疠旱涝之气所致,其传染之毒较六淫之气更强,又怎么可以与大运属寒水之情况相提并论呢?自古而来,运气沒有一定之规律,变化无穷,所以疾病之变化亦因而无常,或补或泻亦沒有常规。今非昔比,亦可知道将来与今日会有不同,但先圣后圣,他们所遵循之原则是一样的,变换一下空间就可以发现都是一样的。如果要当事决断,那就千万不能仿佛。我就这件事上,常常怀着忐忑不安之心,恐伯只是我一家之言而出现失误,所以必须经过反復之验证,基本上有些自信。亦有遇上不可救治之人,明知病人是难以救治的,但仍然这样做,只是出于一份热心肠而已。 |
|
|
1子平:徐子平,名居易,字子平。传说为五代、北宋时占卜师、命理学家。通阴阳五行,集八字、命理之大成。后世之八字推命,多以子平法为正宗,因此「子平」又称为八字、命理学之代称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伤寒温病不识脉,如无目冥行,动辄颠陨。夫脉者,气血之神也,邪正之鑑也。呼吸微茫间,死生关头。若能騐证分明,指下了然,岂有差错耶?伤寒脉法,与杂证自是不同。而温病脉法,与伤寒更是大异。今将长沙、《内经》脉法揭于前,继以陶氏浮中沉三诊脉法,又继以温病与伤寒不同诊脉法。诚能洞晰于此,其于治也庶几乎。 |
|
医治伤寒病与温病不明白脉义,就像盲人在夜间行走,动不动就会跌倒。脉象能反映气血之变化,以及邪气与正气之盛衰。在一呼一吸这个微细动作之间,则是决定病人生死之关头。若果能够验证分明,对于指下之感觉非常清楚,怎么会有过失呢?伤寒病之脉法,与杂病当然是不同。而温病之脉法,与伤寒病更是不同。现在先揭示仲景及《内经》之脉法,然后再揭示陶节庵浮中沉三诊之脉法,最后揭示温病与伤寒病不同之诊脉方法。只要能洞悉以上脉法,对于临床治病也就差不多了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问曰:脉有阴阳何谓也?答曰:凡脉浮、大、动、滑、数,此名阳也;沉、濇、弱、弦、微,此名阴也。阴证见阳脉者生(按:证之阴者,阴极也。脉之阳者,阳生也。阴证阳脉,真阴证也。阳生则阴长,故曰生。如厥阴下利,手足厥逆,脉数,微?汗出,今自愈是也。若脉不数而紧,则死矣),阳证见阴脉者死。河间註云:「脉近于绝故也。」《类经》註云:「证之阳者假实也,脉之阴者真虚也,阳证阴脉即阴证也。」(按:註既曰「假实」,知非真阳。既曰「真虚」,知爲真阴。此假阳证真阴脉,直是阴证似阳也,故註曰即「阴证」也。若火闭而伏,以致脉沉细脱,此真阳证假阴脉,乃是阳证似阴也,非阴证也。辩之不明,死生反掌。) |
问:脉有阴阳,是甚么意思?答:凡是脉浮、大、动、滑、数,这就称为「阳脉」;脉沉、涩、弱、弦、微,这就称为「阴脉」。当阴证见到阳脉时,其人可治(按:如果证候属阴,表明阴寒极盛。而出现阳脉则表示阳气生发。阴证见到阳脉,是真正之阴证。阳生则阴长,所以可治。例如厥阴病见下利,手足厥冷,如果脉数,有微热和出汗,表明其病会自愈。如果脉不数而紧,那就是死证),当阳证见到阴脉时,表示难治。刘河间註:「这是因为脉象几乎消失。」《类经》註:「出现阳证是假实证,而出现阴脉则代表真正之虚证,阳证而有阴脉就是阴证。」(按:注解既然说是「假实」,那就不是真阳。既然说是「真虚」,那就说是真正之阴寒证。这种假阳证而真阴脉,就是阴证似阳,所以註解说「即阴证」。如果火气闭塞而使气机沉伏,导致脉沉细脱,这是真阳证而假阴脉,其实是阳证似阴,不是阴证。辨別不明,极易导致死亡。) |
|
|
寸口脉微,名曰阳不足。阴气上入于阳中,则洒淅恶寒也。尺脉弱,名曰阴不足。阳气下陷入阴中,则发?也。阳脉(浮濡)阴脉弱者,则血虚,血虚则筋急也。其脉(沉弱)者,荣气之微也。其脉(浮濡)而汗出如流珠者,卫气之衰也。(按:「阳脉浮」,「其脉浮」之二「浮」字,应是二「濡」字。若是「浮」字,则与「卫衰,汗出如流珠」之义不属。「其脉沉」之「沉」字,应是「弱」字。若是「沉」字,则与「血虚荣微」之义不属。悉宜改之。) |
寸口脉微,称为「阳不足」。阴气上升进入阳分,就会令人瑟瑟恶寒。尺脉弱,称为「阴不足」。阳气下陷进入阴分,就会导致发热。阳脉(浮濡)而阴脉弱,表示血虚,血虚则筋脉拘急。脉(沉弱)者,反映营气微弱。脉(浮濡)而汗如珠子一样流出者,表示卫气衰弱(按:「阳脉浮」、「其脉浮」这二个「浮」字,应是「濡」字。如果是「浮」字,与「卫衰汗出如流珠」之义不符。「其脉沉」之「沉」字,应是「弱」字。如果是「沉」字,与「血虚营微」之义不符。都应该改过来)。 |
|
|
寸口脉浮爲在表,沉爲在裏,数爲在府,迟爲在藏。若脉浮大者,气实血虚也。 |
寸口脉浮反映表证,脉沉表示裏证,脉数反映腑证,脉迟表示脏证。如果脉浮大,则反映气实而血虚。 |
|
|
寸口脉浮而紧,浮则爲风,紧则爲寒。风则伤卫,寒则伤荣。卫荣俱伤,骨节烦痛,当发其汗也。 |
寸口脉浮而紧,脉浮反映风邪,脉紧表示寒邪。风邪就会伤及卫气,寒邪就会伤及营气。卫气和营气都受到伤害,则出现骨节烦痛,此时应该发汗。 |
|
|
夏月盛?,欲着復衣;冬月盛寒,欲裸其身。所以然者,阳微则恶寒,阴虚则发?也。 |
夏天炎热时,想多穿衣服;冬天严寒时,反而想脱去衣物。之所以会如此,是因为阳虚则恶寒,阴虚则发热。 |
|
|
寸口脉浮大,而医反下之,此爲大逆。浮则无血,大则爲寒。寒气相搏,则爲肠鸣。医乃不知,而反饮冷水,令汗大出。水得寒气,冷必相搏,其人必噎(按:「令汗大出」四字,与上下文义不相连贯,当是衍文,宜删之)。 |
寸口脉浮大,但医者反而用下法,这是完全错误的治法。脉浮则血不足,脉大则为寒。寒邪加上血气虚弱,会引致肠鸣。医者不明于此,反而让患者饮用冷水,导致大量汗出。水受寒气影响,加重阴寒之气,患者必然会噎隔(按:「令汗大出」这四个字,与上下文义不一致,应该是衍文,理应删除)。 |
|
|
诸脉浮数,当发?,而反洒淅恶寒,若有痛处,饮食如常者,当发其痈。脉数不时,则生恶疮也。 |
多数情况下,脉浮数时,应该发热,但反出现瑟瑟恶寒,身体某处疼痛。如果饮食正常,应该会有痈脓。脉数在不应该出现的时间出现,则生恶疮。 |
|
|
伤寒表证,欲发其汗,脉浮有力者,乃可汗之。若浮而无力,或尺脉弱濇迟细者,此真气内虚,不可汗也,汗之则死。伤寒裏证已具而欲下之,切其脉沉有力,或沉滑有力,乃可下之。若沉细无力,或浮而虚者,此真气内虚,不可下也,下之则死。仲景治少阴病,始得之,反发?,脉沉者,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。此太阳少阴之两感也。有太阳之表?,故用麻黄;有少阴之脉沉,故用附子、细辛,发表温裏并行。此证治之奇,脉法之奥,故《内经》曰:「微妙在脉,不可不察也。」 |
伤寒病有表证,如果要发汗,应该在脉浮而有力的情况下才可以发汗。如果脉浮而无力,或者尺脉弱、涩、迟、细,这是真气内虚,不可发汗,如果发汗则会导致死亡。伤寒病裏证已经形成,如果要攻下,诊其脉沉而有力,或者沉滑而有力,才可以攻下。如果脉沉细无力,或脉浮而虚者,这是真气内虚,不可攻下,如果攻下则会导致死亡。仲景治少阴病初起时,反而出现发热,脉沉者,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主治。这属于太阳少阴两感之病。有太阳病之表热,所以用麻黄;又有少阴病之脉沉,所以用附子和细辛,发表和温裏同时进行。由此可见证治之奇特与脉法之奥妙,所以《内经》说:「微妙在脉,不可不察也。」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《内经》曰:「脉至而从,按之不鼓,诸阳皆然。」王太僕註曰:「言病热而脉数,按之不鼓动于指下者,此阴盛格阳而致之,非热也。」又曰:「脉至而从,按之鼓甚而盛也。」王太僕注曰:「言病证似寒,按之而脉气鼓动指下而盛者,此阳甚格阴而致之,非寒也。」东垣治一伤寒,目赤面赤,烦渴引饮,脉息七八至,按之不鼓,此阴盛格阳于外,非热也。用干姜附子汤加人参,数服得汗而愈,亦治法之奇妙也。大抵诊脉之要,全在沉脉中分虚实。如轻手按之脉来得大,重按则无者,乃无根蒂之脉,爲散脉,此虚极而元气将脱也。切不可发表攻裏,如误治之则死,须人参大剂煎饮之。以上所言,乃脉证治例之妙,水火征兆之微,阴阳倚伏之理,要当穷究其旨趣,不可轻易而切之也。 |
《内经》说:「脉至而从,按之不鼓,诸阳皆然。」王冰註解说:「这是指热病而脉数,按脉时在指下沒有鼓动之感,这是阴盛格阳所致,不属于热证。」又说:「脉至而从,按之鼓甚而盛也」。王冰注解说:「这是指病证类似寒证,按脉时在指下明显感到强盛之鼓动感,这是阳盛格阴所致,不属于寒证。」李东垣曾治疗一人病伤寒,目红面红、烦渴欲饮,脉一息七八次,按之指下无鼓动感,此乃阴盛格阳,不是热证。用干姜附子汤加人参,服用数次后汗出而癒,这亦是治法奇妙之处。总的来说,诊脉之关键在于判断沉脉之虚实。如果轻取时脉大,重按则无,此为无根之脉,为散脉,反映极虚而元气将脱。切不可发表或攻裏,如果误治则会导致死亡,应该用大剂量人参煎汤饮用。以上所述是脉证治例反映了水火征兆之微妙,阴阳互根之原理。切脉时需要仔细研究其精髓,不能轻易而草率地切脉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浮诊法:以手轻按于皮肤之上,切其浮脉之来,以察表裏之虚实。尺寸俱浮者,太阳也。浮而紧者为寒在表,浮而数者为热在表。以脉中有力为有神,可汗之。浮而缓者为风在表,可解之,不可汗。浮而无力为虚为无神,不可汗。凡尺脉浮,寸脉浮,俱有力,可汗。若尺脉迟弱者,此真气不足,不可汗也。浮大有力为实为热,可汗之。浮大无力,为虚为散,不可汗也。浮而长,太阳合阳明。浮而弦,太阳合少阳。凡脉浮主表,不可攻裏也。 |
浮诊法:将手指轻轻按在皮肤上,就可以切得浮脉,用以判断表裏之虚实情况。如果浮脉见于寸关尺三部,这是病在太阳。脉浮而紧,说明寒邪在表。脉浮而数,说明热邪在表。脉象有力,表示有脉神,可以发汗。脉浮而缓,表示风邪在表,可以解表但不可发汗。脉浮而无力,表示虚证、脉无神,不可发汗。凡是尺脉浮、寸脉浮,而且有力,可以发汗。如果尺脉迟弱,表示真气不足,不可发汗。如果脉浮大有力,属实为热者,可以发汗。如果脉浮大无力,属虚为气血不足者,不可发汗。脉浮而长,为太阳与阳明合病。脉浮而弦,为太阳与少阳合病。凡浮脉则主表证,不可治裏。 |
|
|
中诊法:以手不轻不重,按至肌肉之分而切之,以察阳明、少阳二经之脉也。尺寸俱长者,阳明也。浮长有力则兼太阳,表未解也,无汗者宜发汗。长而大,有力为热,当解肌。长而数,有力为热甚,当平热也。长洪、长滑有力,此胃中实热,可攻之也。尺寸俱弦者,少阳也,宜和之。浮弦有力兼太阳,表未解也,可发汗。弦洪、弦长、弦数、弦滑有力为热甚,宜清解之。弦迟、弦小、弦微皆内虚有寒,宜温之也。凡弦脉只可和,不可汗下,不可利小便也。 |
中诊法:以不轻不重之力将手指按压至肌肉部位来切脉,用以观察阳明经和少阳经之脉象。寸关尺脉三部脉俱长,这是病在阳明。脉浮长有力,则同时病兼太阳之表证未解,无汗者就应该发汗。脉长大而有力,为有热,应当解肌。脉长而数且有力,为热甚,需要清热。脉长洪、长滑而有力,胃中有实热,可攻下。寸关尺三部脉俱弦,这是病在少阳,应当和解。脉浮弦有力,则同时病兼太阳之表证未解,可以发汗。脉弦洪、弦长、弦数,弦滑有力,为热甚,应当清解热邪。脉弦迟、弦小、弦微,都属于内虚有寒,应当温补。凡是弦脉只能和解,不宜发汗、攻下,也不宜利小便。 |
|
|
沉诊法:重手按至筋骨之分而切之,以察裏证之虚实也。尺寸俱沉细者太阴也,俱沉者少阴也,俱沉弦者厥阴也。沉疾、沉滑、沉实为有力有神,为阳盛阴微,急宜滋阴以退阳也。沉迟、沉细、沉微为无力无神,为阴盛阳微,急宜生脉以回阳也。大抵沉诊之脉,最为紧关之要,以决阴阳寒热,用药死生在毫髮之间。脉中有力为有神,为可治。脉中无力为无神,为难治。用药宜守而不宜攻,宜补而不宜泻也。 |
沉诊法:将手指重力按压至筋骨部位来切脉,观察裏证之虚实。寸关尺三部脉俱沉细者,病在太阴。俱沉者,病在少阴。俱沉弦者,病在厥阴。脉沉疾、沉利、沉实而有力者,为有脉神,属于阳盛阴微,急需滋养阴气以退却阳邪。脉沉迟、沉细、沉微而无力者,为脉无神,属于阴盛而阳微,急需生脉以回阳。一般而言,沉诊最紧要之处是在于决定阴阳、寒热之关键,用药决定病者之生死只在毫髮之间。脉气有力为有脉神,属于可治。脉气无力为脉无神,属于难治。用药时应该以固护为主而非攻邪,应当以补益为主而非泻下。 |
|
原文 |
翻译 | |
|
凡温病脉不浮不沉,中按洪、长、滑、数,右手反盛于左手,总由怫?郁滞,脉结于中故也。若左手脉盛,或浮而紧,自是感冒风寒之病,非温病也。 |
温病之脉不浮不沉,中按脉洪、长、滑、数,右手脉反而盛于左手,总是因为热邪郁滞于中。如果左手脉盛,或浮而紧,这通常是冒受风寒所致之病,而不是温病。 |
|
|
凡温病脉,怫?在中,多见于肌肉之分而不甚浮,若?郁少阴,则脉沉伏欲绝,非阴脉也,阳邪闭脉也。 |
凡温病之脉,中有郁热,常见于肌肉之部,通常不见到明显之脉浮。如果有热邪郁滞在少阴,则脉沉伏欲绝,这并非阴脉,而是阳邪阻闭脉气所致。 |
|
|
凡伤寒自外之内,从气分入,始病发?恶寒,一二日不作烦渴,脉多浮紧。不传三阴,脉不见沉。温病由内达外,从血分出,始病不恶寒而发?,一?即口燥咽干而渴,脉多洪滑,甚则沉伏。此发表清裏之所以异也。 |
凡伤寒病是由外入内,由气分而入,初起时发热恶寒,一两天内不会有烦渴,脉多见浮紧。未传至三阴,不会出现沉脉。而温病是从内达于外,从血分而出,初起不恶寒但发热,一发热就会口干咽燥而渴,脉多为洪,甚至沉伏。这是伤寒病与温病初起时发表或清裏不同治法之由来。 |
|
|
凡浮诊中诊,浮大有力,浮长有力,伤寒得此脉,自当发汗,此麻黄、桂枝证也。温病始发,虽有此脉,切不可发汗,乃白虎、泻心证也。死生关头,全于此分。 |
凡是诊脉,浮取或中取时,脉浮大有力,或浮长有力,伤寒病得此脉,自然应该发汗,这就是麻黄汤证、桂枝汤证。温病刚开始发病时,即使有此脉象,切不可发汗,而是白虎汤证、泻心汤证。生死关头,全在这一点上分辨。 |
|
|
凡温病内外有?,其脉沉伏,不洪不数,但指下沉濇而小急,断不可误爲虚寒。若以辛温之药治之,是益其?也。所以伤寒多从脉,温病多从证。盖伤寒风寒外入,循经传也。温病拂?内炽,溢于经也。 |
凡温病内外有热,脉沉伏,不洪不数,但是指下沉涩而小急,千万不能将此误认为是虚寒。如果用辛热之药治疗,只会加重邪热。这就是为甚么伤寒病多从脉象来判断,而温病多从证候来判断的原因。因为伤寒病是风寒从外侵入,循经传变。而温病是郁热内盛,泛溢于经络。 |
|
|
凡伤寒始本太阳,发?头痛而脉反沉者,虽曰太阳,实见少阴之脉,故用四逆汤温之。若温病始发,未尝不发?头痛,而见脉沉濇而小急,此伏?之毒滞于少阴,不能发出阳分,所以身大?而四肢不?者,此名「厥」。正杂气怫郁,火邪闭脉而伏也,急以咸寒大苦之味,大清大泻之。断不可误爲伤寒太阳始病,反见少阴脉沉,而用四逆汤温之,温之则坏事矣(眉批:于脉中即见得异,此发前人所未到之旨也)。又不可误爲伤寒阳厥,慎不可下,而用四逆散和之,和之则病甚矣。盖?郁亢闭,阳气不能交接于四肢,故脉沉而濇,甚至六脉俱绝,此「脉厥」也。手足逆冷,甚至通身冰凉,此「体厥」也,即仲景所谓阳厥,「厥浅?亦浅,厥深?亦深」是也。下之断不可迟,非见真守定,通权达变者,不足以语此(眉批:此段议论,乃千古特识。患温者,从此不冤矣。俗医何曾梦见)。 |
凡伤寒病通常始于太阳,发热头痛而脉象反沉,虽然说病在太阳,实际上已经见到少阴病之脉,因此需要用四逆汤来温补。如果温病初起,未尝不会出现发热头痛,但脉象却沉涩小急,这是伏热之毒滞于少阴而不能发出到阳分,所以会身体高热但四肢不热,这就被称为「厥」。正气与杂气闭郁于内,火邪阻闭气机而使脉伏,需要立刻用咸寒大苦之药物,有力清泻热邪。决不能错误地认为这是伤寒病太阳证初起而见少阴之脉,便用四逆汤来温补,那样将会加重病情(眉批:从脉象中就可见两病之不同,这真是说出了前人所沒说过的)。也不能误认为是伤寒病之阳厥,以为阳厥不可攻下,便用四逆散和之,和之则将会加重病情。因为郁热之邪亢盛,闭阻气机而使阳气无法达于四肢,所以脉沉而涩,甚至六部脉象消失,这是「脉厥」。手足逆冷,甚至全身冰凉,这是「体厥」,即是仲景所说阳厥之「厥浅热亦浅,厥深热亦深」。对于这种情况,断不可延迟运用攻下法。对于沒有认识并坚守这种真知灼见,而且能通权达变之人,是无法与其说清这个道理的(眉批:这段议论可以说是千古卓见。患温病者,从此不再被冤死。这是庸医做梦都不会想到的)。 |
|
|
凡温病脉,中诊洪长滑数者轻,重则脉沉,甚则闭绝。此辩温病与伤寒,脉浮脉沉异治之要诀也。 |
凡温病之脉,中取则洪长滑数,而重按则脉沉,甚至闭塞而无脉。这是区別温病和伤寒病,根据其浮脉和沉脉来加以不同治疗的关键。 |
|
|
凡温病脉,洪长滑数,兼缓者易治,兼弦者,难治。 |
凡温病之脉洪、长、滑、数,同时兼缓者易治,而兼弦者则难治。 |
|
|
凡温病脉,沉濇小急,四肢厥逆,通身如冰者,危。 |
凡温病之脉沉、涩、小、急,见有四肢厥逆,全身冰冷者,属于病危。 |
|
|
凡温病脉,两手闭绝,或一手闭绝者,危。 |
凡温病之脉两手脉绝,或者一手脉绝者,属于病危。 |
|
|
凡温病脉,沉濇而微,状若屋漏者,死。 |
凡温病之脉沉涩而微,脉象如房屋漏水,属于死证。 |
|
|
凡温病脉,浮大而散,状若釜沸者,死。 |
凡温病之脉浮大而散,犹如锅中之沸水,属于死证。 |
|
|
按:伤寒温病,必须诊脉施治。有脉与证相应者,则易于识別。若脉与证不相应,却宜审察缓急,或该从脉,或该从证,务要脉证两得。即如表证,脉不浮者可汗而解。裏证,脉不沉者,可下而解。以邪气微,不能牵引,抑郁正气,故脉不应。下利脉实有病愈者,但得证减,復有实脉,乃天年脉也。又脉法之辨,以洪滑者爲阳爲实,以微弱者爲阴爲虚,不待问也。然仲景曰「若脉浮大者,气实血虚也」,《内经》曰「脉大四倍以上爲关格」,皆爲真虚。陶氏曰:「不论浮沉大小,但指下无力,重按全无,便是阴脉。」此洪滑之未必尽爲阳也、实也。景岳曰:「其脉如有如无,附骨乃见,沉微细脱,乃阴阳潜伏闭塞之候。」陶氏曰:「凡内外有?,其脉沉伏,不洪不数,指下沉濇而小急,是爲伏?。」此微弱之未必尽爲阴也、虚也。夫脉原不可一途而取,须以神气、形色、声音、证候,彼此相参,以决死生安危,方爲尽善。所以古人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者,缺一不可。 |
按:对于伤寒病和温病,必须依靠脉象与证候进行治疗。当脉象与证候所反映的情况相符,就很容易识別。但如果脉证不相符,就需要仔细审察其缓急,或依据脉象,或依据证候,务必要从脉证两方面加以考察。比如表证,即使脉不浮,亦可以通过发汗来解除。而裏证,即使脉不沉,亦可以通过攻下来解除。由于邪气微弱,影响不大,抑制了正气,所以脉象不能与证候相应。下利而脉象有力者,病情好转之后,仍然是实脉,这是病人自然之脉。就脉法而言,以脉洪滑者属阳、属实,以脉微弱者属阴、属虚,这是无需问了。但是,仲景却说:「如果脉浮大,属于气实而血虚。」《内经》又说:「脉象比平时大于四倍者为关格。」这都属于真虚。陶氏说:「脉象不论浮沉大小,只要指下无力,重按完全沒有感觉,就是阴脉。」所以脉洪滑未必都是属阳、属实。张景岳说:「脉象似有似无,重按至骨才能感觉到沉、微、细、脱之脉,这是阴阳气被潜伏闭塞之征兆。」陶氏又说:「凡是内外有热而脉象沉伏,不洪不数,指下沉涩而小急,这是伏热之征兆。」所以微弱之脉未必都是属阴、属虚。对于脉象之判断原本就不能只有单一方法,需要结合神气、形色、声音、证候等相互参照,从而决定病者之生死安危,这样做才算是尽善尽美。所以古人认为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缺一不可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太阳经病,头项痛,腰嵴强,身痛,发?恶寒,恶风,脉浮紧。以太阳经脉由嵴背连风府,至巅鼎,故为此证。此三阳之表也(仲景曰:「大汗后,身?愈甚者,阴阳交而魂魄离也」)。 |
|
太阳经病,头项疼痛、腰背强直、身痛、发热恶寒、恶风,脉浮紧。这是由于太阳经循行嵴背而上连风府,直达巅顶,所以表现为这些证候。这是三阳之表病。(仲景说:「大汗之后,身热更加严重者,其病为阴阳交而魂魄离散」)。 |
|
阳明经病,身?,目痛,鼻干,不眠,脉洪而长。以阳明主肌肉,其脉挟鼻,络于目,故为此证。此三阳之裏也。正阳明府病,由表传裏,由经入府也。邪气既深,故为潮?,自汗,谵语,发渴,不恶寒,反恶?,揭去衣被,扬手掷足,或发斑黄狂乱,五六日不大便,脉滑而实,此实?已传于内,乃可下之。若脉弱无神,又当详辩。 |
|
阳明经病,身热、目痛、鼻干、不眠,脉洪而长。由于阳明主肌肉,其脉循行于鼻而络于目,所以表现为这些证候。这是三阳之裏病。正阳明阳明之腑病是邪气由表传裏,由经络传入于腑。邪气已经深入,所以表现为潮热、自汗、谵语、口渴、不恶寒、反恶热、扯去衣被、抓手踢脚,或发斑、发黄、狂乱,五六天不大便,脉滑而实,这反映了实热已传入胃明之腑,才可以攻下。如果脉弱无神,则需要详细辨別。 |
|
少阳经病,往来寒?,胸脇满痛,默默不欲食,心烦喜呕,口苦,目眩,耳聋,脉弦而数。以少阳经脉循胁肋,络于耳,故为此证。此三阳三阴之间也。由此渐入三阴,故为半表半裏之证(伤寒邪在三阳,但有一毫表证,总以发汗解肌为主)。 |
|
少阳经病,寒热往来、胸胁胀痛、默默不欲食、心烦喜呕、口苦、目眩、耳聋,脉弦而数。由于少阳经循胁肋而络于耳,所以表现为这些证候。这是三阳三阴之间之病变。由此就会逐渐进入三阴,所以属于半表半裏之病证(伤寒邪气在三阳时,只要有一丝一毫的表证,总要以发汗解肌为主)。 |
|
太阴经病,腹满而吐,食不下,嗌干,手足自温,或自利,腹痛,不渴,脉沉而细,以太阴经脉布胃中,络于嗌,故为此证。 |
|
太阴经病,腹满而呕吐、不能食、咽喉干燥、手足自温,或自利、腹痛、不渴,脉沉而细。由于太阴经布散胃中而络于咽喉,所以表现为这些证候。 |
|
少阴经病,欲吐不吐(脉注胸,邪上逆),心烦(络心,故烦),但欲寐(阴主静),口燥舌干,自利而渴(络心,故干渴),或咽痛,吐利,引衣蜷卧(寒主收引,故蜷卧),其脉沉。以少阴经脉贯肾络于肺,系舌本,故为此证。 |
|
少阴经病,欲吐而不能吐(其脉贯注胸中,邪气上逆)、心烦(其脉络心,故烦躁)、但欲寐(阴主静)、口干舌燥、下利而口渴(其脉络心,故口渴)、或咽痛、呕吐、下利,裹紧衣服而踡卧(寒主收引,故踡卧),脉沉细。由于少阴经贯肾而络于肺,与舌根相连,所以表现为这些证候。 |
|
厥阴经病,烦满,囊缩(脉循阴器),消渴(子盛则母虚,故肾水消而生渴),气上撞心,心中痛?(母盛则子实,故气撞心而痛?),飢不欲食,食即吐蛔(木邪则土受伤),下之利不止,脉沉而弦。以厥阴经脉循阴器。络于肝,故为此证。 |
厥阴经病,烦躁,阴囊收缩(其脉循阴器),消渴(子盛则母虚,所以肾水不足而引发口渴)、气上撞心,心中疼热(母盛则子实,所以气撞心而疼痛有热感)、饥不欲食,进食后则吐蛔(木邪盛而犯土气),下之则下利不止,脉沉而弦。由于厥阴经循阴器而络于肝,所以表现为这些证候。 |
|
|
按:伤寒自外之内,脉证一定,而传变无常,但不可拘于日数,泥于次序。《内经》次第言之者,以发明其理耳。大抵太阳表证居多,然岂无初病径犯阳明者?岂无发于太阳即少阴受之者?岂无太阳?郁以次而传三阴者?岂无太阳止传阳明、少阳而不传三阴者?所以仲景有云:「日数虽多,有表证即宜汗;日数虽少,有裏证即宜下。」此二句语活而义广,治伤寒之良法也。 |
按:伤寒病由表入裏,有其较为固定之脉证,但传变则变化无穷,只是不能以日数或次序来推断。《内经》用次序来分辨伤寒病不同阶段,只是为了阐明其发病之理。一般而言,太阳病以表证最为常见,难道沒有初病时直接侵袭阳明的吗?难道沒有从太阳病就直接传变而成少阴病的吗?难道沒有太阳病之热郁依次传至三阴的吗?难道沒有太阳病只传阳明或少阳而不传三阴的吗?所以仲景说:「发病日数虽多,若有表证就宜发汗;发病日数虽少,若有裏证就宜用攻下。」这两句话灵活而含义广泛,是治疗伤寒病之良法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《伤寒论·平脉篇》曰:「寸口脉阴阳俱紧者,法当清邪中于上焦,浊邪中于下焦。清邪中上名曰洁也,浊邪中下名曰浑也。(旁批:慄山曰:「此段乃温病脉证根源也,虽未明言温病,其词意与伤寒绝不相干。《温疫论》以温病得于杂气,《缵论》以温病由血分出,观此益信」)。阴中于邪,必内慄也」(慄,竦缩也。按:《经》曰「清邪」,曰「浊邪」,明非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气之邪也,另为一种,乃天地之杂气也。种种恶秽,上溷空明清净之气,下败水土污浊之气,人受之,故上曰「洁」,下曰「浑」,中必「内慄」也)。 |
《伤寒论·平脉篇》说:「寸口脉阴阳俱紧者,法当清邪中于上焦,浊邪中于下焦。清邪中上名曰洁也,浊邪中下名曰浑也。(旁批:杨慄山注:「这段内容实际上是温病脉证之根源,儘管沒有明确提及温病,但其所表达之意思与伤寒病无关。《温疫论》认为温病是由杂气所引发,《伤寒缵论》认为温病始于血分,由此看来就更加可信」)。阴中于邪,必内慄也」(慄,身体怕冷而紧缩。按:《经》文中说「清邪」、「浊邪」,明明不是指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气之邪,而是另一种,即天地之杂气。各种恶秽之气上升而混杂于清阳之中,下沉则使水土之气变得污浊,人感受之,所以在上称为「洁」,在下称为「浑」,在中必然会「内慄」。) |
|
|
玩篇中此四十六字,全非伤寒脉证所有事,乃论温病所从入之门,变证之总,所谓「赤文绿字,开天闢地之宝符」,人未之识耳(眉批:仍从《伤寒论》中看出,温病得于杂气,与伤寒外感风寒不同,是读书得间处)。大意谓人之鼻气通于天,如毒雾烟瘴谓之「清邪」,是杂气之浮而上者,从鼻息而上入于阳。而阳分受伤(旁批:《经》云「清邪中上焦」是也),久则发?头肿,项强颈挛,与俗称「大头温」、「虾蟆温」之说符也。人之口气通于地,如水土物产化为「浊邪」,是杂气之沉而下者,从口舌而下入于阴,而阴分受伤(旁批:《经》云「浊邪中下焦」是也)。久则脐筑湫痛,呕泻腹鸣,足膝厥逆,便清下重,与俗称「绞肠温」、「软脚温」之说符也。然从鼻从口所入之邪,必先注中焦,分布上下,故中焦受邪(旁批:《经》云「阴中于邪」是也),则清浊相干,气滞血凝不流,其酿变即现中焦,与俗称「瓜瓤温」、「疙瘩温」、「阳毒」、「阴毒」之说符也。此三焦定位之邪也(眉批:奇想天开,妙有至理,温病之来歷,从此復明于世矣)。气口脉盛属内伤,洪长滑数,阴阳搏激曰「紧」。若三焦邪溷为一,则怫郁熏蒸,口烂蚀断。卫气通者,游行经络藏府,则为痈脓。荣气通者,嚏出声嗢咽塞,?壅不行,则下血如豚肝,如屋漏。然以荣卫渐通,犹非危候。若上焦之阳,下焦之阴,两不相交,则脾气于中难运,斯五液注下,而生气几绝矣。《缵论》所谓「伤寒自气分传入血分,温病由血分发出气分」,铁案不移。伤寒得天地之常气,先行身之背,次行身之前,次行身之侧。自皮肤传经络,受病于气分,故感而即动。认真脉证治法,急以发表为第一义,入裏则不消矣。未有温覆而当不消散者,何至传入血分,变证百出哉?河间以「伤寒为杂病,温病为大病」,信然。盖温病得天地之杂气,由口鼻入,直行中道,流布三焦,散漫不收,去而復合,受病于血分,故郁久而发。亦有因外感,或飢饱劳碌,或焦思气恼触动而发者。一发则邪气充斥奔迫,上行极而下,下行极而上,即脉闭体厥,从无阴证,皆毒火也。与伤寒外感,与治伤寒温散,何相干涉(眉批:伤寒以脉为主,温病以证为主)?奈何千年愦愦,混为一病,试折衷于经论,宁不涣然冰释哉?治法急以逐秽为第一义。「上焦如雾」,升而逐之,兼以解毒;「中焦如沤」,疏而逐之,兼以解毒;「下焦如渎」,决而逐之,兼以解毒。恶秽既通,乘势追拔,勿使潜滋。所以温病非泻则清,非清则泻,原无多方,时其轻重缓急而救之。或该从证,或该从脉,切勿造次。 |
仔细品味《伤寒论》中这四十六字,完全与伤寒病之脉证无关,而是从总体上论述了温病的起源和变化,犹如「赤文绿字,乃开天闢地之宝符」,只不过人们沒有意识到罢了(眉批:这仍然是从《伤寒论》中看出,温病得之于杂气,与伤寒病由于外感风寒是不同的,是读书之间所得到的)。大意是指人之鼻气通于天,如有毒雾烟瘴则称之为「清邪」,这是杂气中浮上来的部分,通过鼻息而进入阳分。而阳分受伤(旁批:即《经》文中所说的「清邪中于上焦」),久而发热头肿,颈强颈挛,与俗称「大头温」、「虾蟆温」之说法相符。人之口气通于地,如水土之物产化而为「浊邪」,这是杂气中沉下去的部分,通过口舌而进入阴分。而阴分受伤(旁批:即《经》文中所说的「浊邪中于下焦」),日久则脐腹绞痛,呕吐,泄泻,肠鸣,足膝厥逆,下利而后重,与俗称「绞肠温」、「软脚温」之说法相符。然而,从鼻和口所入之邪气,必然先注入中焦,再分布于上下焦,所以中焦受邪(旁批:即《经》文中所说的「阴中于邪」),则清浊之气相干,气滞血凝而不流,其病变即现于中焦,与俗称「瓜瓤温」、「疙瘩温」、「阳毒」、「阴毒」之说法相符。这就是用三焦来定位邪气在(眉批:真是奇想天开,特別有道理,温病来来源,从此再次在世间清晰了)。气口脉盛属于内伤,脉洪长滑数,阴阳搏击称为「紧」。如果三焦之邪混而为一,则会郁结而薰蒸,导致口烂溃疡。如果卫气通畅,则会游行于经络脏腑中,发而为痈脓。如果营气通畅,则会引发喷嚏,声音嘶哑,喉咙阻塞,热邪壅滞,而导致大便出血如猪肝状,如屋漏一样不止。但是因为营卫渐渐通畅,这些还不是危险证候。如果上焦之阳气与下焦之阴两者不相交,则脾气在中焦难以运行,如此五液就会注入下焦,生机几乎要灭绝了。《伤寒缵论》中所说的「伤寒自气分传入血分,温病由血分发出气分」,真是确凿无疑。伤寒病是感受天地之常气,首先侵犯身体背部,然后是是前部,再然后是侧面。从皮肤传入经络,犯于气分,因此感受邪气后就立即发病。只要明确伤寒病之脉证,第一时间就应该发表,如果邪气入裏则难以消散。只要服药后盖被发汗,邪气自当消散,怎会还有传入血分,出现各种变证呢?刘河间认为「伤寒为杂病,温病为大病」,确实是这样的。因为温病是发于天地之杂气,通过口鼻而入,直犯中焦,然后布散于三焦,散漫不收,然后又重新聚合,犯于血分,所以郁久才会发作。也有因为外感,或饥饱劳碌,或焦虑气恼触动而发作。一旦发作,则邪气充斥奔迫,上行极而后下行,下行极而后上行,即使是脉道闭塞,身体厥冷,也从来沒有阴证,都属于毒火所致。这与伤寒病外感邪气,与治疗伤寒病而用温散,又有什么关系呢(眉批:伤寒病以辨脉为主,温病则以辨证为主)?无奈何,千百年来对此认识不清而将伤寒与温病混为一病,只是试图在经论中寻求折中之说法,难道就不能使其涣然冰释吗?治疗温病在治法上就应该首先驱除秽浊之邪。「上焦如雾」,就需要「升而逐之」,同时解毒;「中焦如沤」,就需要「疏而逐之」,同时解毒;「下焦如渎」,就需要「决而逐之」,同时解毒。秽浊之邪一旦被逐,就要顺势追击,不让其潜伏郁结。所以治疗温病不是泻下就是清解,不是清解就是泻下,原本无需多种方法,只要根据其轻重缓急加以救治。或应该以证候为主,或应该以脉象为主,千万不要弄错了。 |
|
|
《伤寒论》曰:「凡治温病,可刺五十九穴。」(旁批:此段明言温病治法与伤寒不同) |
《伤寒论》说:「凡治温病,可刺五十九穴。」(旁批:这段文字明言温病与伤寒病之治法是不同的)。 |
|
|
成註以「泻诸经之温?」,谓泻诸阳之?逆,泻胸中之?,泻胃中之?,泻四肢之?,泻五藏之?也。 |
成无己以「泻诸经之温热」为,是指泻去诸阳经之热邪上逆,即泻去胸中之热邪,泻去胃中之热邪,泻去四肢之热邪,泻去五脏之热邪。 |
|
|
按:温病脉,《经》曰「寸口脉阴阳俱紧」,与伤寒脉浮紧、浮缓不同。温病证,《经》曰「中上焦」,「中下焦」,「阴中邪」(升降散、增损双解散主方也),与伤寒证,行身背,行身前,行身侧不同。温病治法,《经》曰「刺五十九穴」,与伤寒治法温覆发散不同。非以温病,虽有表证,实无表邪,明示不可汗耶?独是河间以伤寒为杂病,三百九十七法,一百一十三方,至详且悉。温病为大病,岂反无方论治法乎?噫!兵燹散亡,传写多讹,错简亦復不少。承讹袭谬,积习相沿,迄今千余年矣。名手林立,方书充栋,未有不令发汗之说。馀一人以管窥之见,而欲革故洗新,使之从风,亦知其难。然而孰得孰失,何去何从,必有能辩之者。 |
按:温病之脉象,《经》文说是「寸口脉阴阳俱紧」,这与伤寒病之脉浮紧、浮缓不同。温病之证候,《经》文说是「中上焦」、「中下焦」、「阴中邪」(升降散、增损双解散为主方),这与伤寒病之证候在身背部、身前部、身侧部不同。温病之治法,《经》文说是「刺五十九穴」,这与治伤寒病用温覆发散之治法不同。难道这不是因为温病虽然有表证,但实际上却沒有表邪,所以明确示人不可发汗吗?惟独刘河间将伤寒视为杂病,将《伤寒论》中三百九十七法和一百一十三方进行详尽而全面之解释。温病作为一种重大疾病,难道沒有其相应的治法和方剂吗?唉!由于兵火战乱而使经书亡轶,而在流传过程中又多传写错误,错简亦不少。医家承袭了错误,积习不改,相传至今已有千余年。虽然名医林立,方书充栋,沒有一个不是主张发汗之说法。我一个人以窥管之见,而想改弦更张,使之随风转变,也知道其困难。然而究竟谁对谁错,何去何从,必然会有能者加以判別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西汉张仲景着《卒病伤寒论》十六卷,当世兆民赖以生全。至晋代不过两朝相隔,其《卒病论》六卷已不可復睹。即《伤寒论》十卷,想亦劫火之余,仅得之读者之口授,其中不无残阙失次。赖有三百九十七法,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,可为校正。而温病失传,王叔和搜讨成书,附以己意,指为伏寒,插入异气,似近理而弥乱真。其《序例》有曰:「冬时严寒杂厉之气,中而即病者为伤寒。中而不即病,寒毒藏于肌肤,至春变为温病,至夏变为暑病。」成无己註云:「先夏至为病温,后夏至为暑病,温暑之病本于伤寒而得之。」由斯以谈,温病与伤寒同一根源也,又何怪乎?后人治温病,皆以伤寒方论治之也。殊不知温病另为一种,非寒毒藏至春夏变也。自叔和「即病」、「不即病」之论定,而后世名家方附会之不暇,谁敢辩之乎?馀为拨片云之翳,以着白昼之光。夫严寒中人顷刻即变,轻则感冒,重则伤寒,非若春夏秋风暑湿燥所伤之可缓也。即感冒一证之最轻者,尚尔头痛身痛,发热恶寒,四肢拘急,鼻塞痰喘。当即为病,不能容隐。今为严寒杀厉所中,反能藏伏过时而变,谁其信之?更问何等「中而即病」?何等「中而不即病」?何等「中而即病」者,头痛如破,身痛如杖,恶寒项强,发热如炙,或喘或呕,烦躁不宁,甚则发痉,六脉如弦,浮紧洪数。传变不可胜言,失治乃至伤生?何等「中而不即病」者,感则一毫不觉,既而挨至春夏?当其已中之后,未发之前,神气声色不变,饮食起居如常?其已发之证,势更烈于伤寒?况风寒侵入,未有不由肌表而入,所伤皆同荣卫,所中均系严寒。一者何其灵敏,感而遂通?一者何其痴呆,寂然不动?一本而枝殊,同源而流异,此必无之事。歷来名家无不奉之为祖,所谓「千古疑城,莫此难破」。然而孰得孰失,何去何从,芸夫牧竖1 ,亦能辩之(眉批:人皆知仲景之法自叔和而明,不知亦自叔和而晦,温病之坏始此矣。后贤先传,后经附会阐发,为叔和功臣,非仲景功臣也。兹欲溯仲景渊微,必先破叔和藩篱。譬诸五谷虽为食宝,设不各为区別,一概混种混收,鲜不贻耕者食者之困矣)。再问何等「寒毒藏于肌肤」?夫肌为肌表,肤为皮之浅者,其间一毫一窍,无非荣卫经行所摄之地,即偶尔脱衣换帽所冒些小风寒,当时而嚏,尚不能稽留。何况严寒杀厉之气,且藏于皮肤最浅之处,反能容忍至春,更歷春至夏发耶?此固不待辩而自屈矣(旁批:慄山曰:「予颇明读书之利害,王安石遵信《周礼》,何如前人蹈弊。医虽小道,是乃仁术也,所以辩之亲切恳至乃而」)。乃又曰:「须知毒烈之气,留在何经而发何病」,前后不答,非故自相矛盾,其意实欲为异气四变,作开山祖师也。后人孰知其为一场懵懂乎?予岂好辩哉!予不得已也(眉批:此曰「毒烈之气,留在何经而发何病」,却是正论,却是翻自己的案。可知「中而不即病,寒毒藏于肌肤」之说,于理大谬矣。质之叔和,何辞以对)。凡治伤寒大法,要在表裏分明。未入于府者,邪在表也,可汗而已。已入于腑者,邪在裏也,可下而已。若夫温病,果系寒毒藏于肌肤,延至春夏犹发于表,用药不离辛温,邪气还从汗解,令后世治温病者,仍执肌肤在表之寒毒,一投发散,非徒无益而又害之。且夫世之凶厉大病,死生人在反掌间者,尽属温病,发于冬月正伤寒者,千百一二。而方书混同立论,毫无分別。总由王叔和序《伤寒论》于散亡之余,将温病一门失于编入,指为「伏寒」、「异气」,妄立「温疟」、「风温」、「温毒」、「温疫」四变,插入《伤寒论》中混而为一,其证治非徒大坏而将泯焉。后之学者,殆自是而无所寻逐也已。馀于此道中,已三折其肱矣。兼以阅歷之久,实见得根源所出(眉批:南山可移,此案不可动)。伤寒得天地之常气,风寒外感,自气分而传入血分。温病得天地之杂气,邪毒内入,由血分而发出气分(旁批:「常气」、「杂气」之说,出自《温疫论》。「气分」、「血分」之说,出自《缵论》,皆是千古特识。本此以辩温病与伤寒异,辩治温病与治伤寒异,非杜撰也)。一彼一此,乃风马牛不相及也。何以言之?「常气」者,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,天地四时错行之六气也。「杂气」者,非风、非寒、非暑、非湿、非燥、非火,天地间另为一种,偶荒旱潦疵疠烟瘴之毒气也。故「常气」受病,在表浅而易。「杂气」受病,在裏深而难(眉批:《温疫论》「杂气」一语,开温病无穷法门,《缵论》「血分」一语,开温病无穷方论。乡外人家见有发热、头痛、谵语者,大家惊恐呼为「杂疾」,此却适中病根。习而不察者,吾辈也)。就令如《序例》所云「寒毒藏于肌肤,至春夏变为温病暑病」,亦寒毒之自变为温,自变为暑耳。还是冬来常气,亦犹「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」之说,于杂气何与?千古流弊,只缘人不知疵疠旱潦之杂气而为温病,遂与伤寒视而为一病,不分两治。馀固不辞谫陋,条分缕析,将温病与伤寒辩明,各有病原,各有脉息,各有证候,各有治法,各有方论。令医家早为突曲徙薪之计,庶不至焦头烂额耳。 |
西汉张仲景着《卒病伤寒论》共十六卷,当时万民因此而能保全生命。从汉至晋相隔不过二个朝代,其中《卒病论》六卷已经失传。即使是《伤寒论》十卷,想来也是因为战火之劫,只能靠读者之口授相传而流传下来,其中也不无残缺或前后失去顺序。幸好还有三百九十七法和一百一十三方可以进行校正。然而,温病部分则失传了,王叔和在搜集成书之过程中附和了他个人之看法,插入了「伏寒」和「异气」等概念,看似有理,但却以假乱真。他在《伤寒例》中说:「冬时严寒杂厉之气,中而即病者为伤寒。中而不即病,寒毒藏于肌肤,至春变为温病,至夏变为暑病。」成无己注解说:「先夏至日发病者为温病,后夏至日发病者为暑病,温病和暑病原本都是伤于寒所引发。」从这个角度来看,温病和伤寒病都是同一根源,这有什么奇怪呢?所以后来治疗温病都是按治伤寒病之方法治疗。却不知道温病是另一种疾病,不是寒毒藏到春夏才变成的。自从王叔和提出「即病」、「不即病」之说成为定论之后,后世名家都纷纷附会,有谁敢辩驳呢!我只是想拨开云雾,让白昼之光明显现。严寒伤人即刻就会使人发病,轻则感冒,重则得伤寒病,不像春夏秋季之风暑湿燥邪气所伤而缓慢地发病。即使是最轻微之感冒,仍然会有头痛、身痛、发热恶寒、四肢拘急、鼻塞和咳痰等证。即时发病,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。现在被严寒杀厉之气所伤,邪气反而能伏藏起来,再过一段时间才会使人生病,谁会相信呢?再问一问,甚么时候会「中而即病」?甚么时候会「中而不即病」?什么情况下「中而即病」者,头痛如破,身痛如被杖打,恶寒,项强,高热,或喘或呕,烦躁不安,甚则抽搐,六脉如弦,或脉浮紧洪数。疾病之变化多不可数,只有失治之后才会危及生命吗?什么情况下「中而不即病」者,在感受邪气后毫无觉察,直到春夏季才有感觉?在其已经受寒而尚未发病之前,神气声色都沒有变化,饮食起居亦都正常吗?而发病之后证候,其病势则比伤寒病更为剧烈?何况风寒邪气侵入时,沒有不经过肌肤而入。都是营卫气受到伤害,都是风寒邪气伤人。为什么有些人如此敏感,感受即发病?而有些人却呆若木鸡,毫无反应呢?一颗树长出不同树枝,同一水源却有不同之支流,这本来就是沒有的事。歷代名家却无不将其奉为始祖,这就是所谓的「千古疑城,莫此难破」。然而谁对註错,何去何从,连农夫牧童都能分辨清楚(眉批:人们都知道仲景之书是经过王叔和整理后传世,但不知道也是因为王叔和而导致很多误解,对温病认识之混乱就是由此始起。后来之学者将其传承下来,再经过附会发挥,都成了叔和之功臣,而非是仲景之功臣。要想重新发挥仲景之思想,必须先打破叔和之观点。比如,虽然五谷都是食物之珍宝,但如果不进行区分,一律混在一起进行播种与收割,一定会引起耕种者和食用者之困惑)。再问一问,甚么是「寒毒藏于肌肤」?肌是指肌表,肤是指最外层的皮肤,肌肤上一毫一窍都是营卫循行并管辖之区域,即使偶尔脱衣换帽时感受到一点点风寒,即刻就会喷嚏而不会拖延太久。更何况严寒杀厉之气,而且只是藏于皮肤最浅层,反而能拖延到春季,再经歷春季再到夏季才发病?这种说法无需辩驳就已经无话可说了(旁批:杨慄山说:「我深明白读书之利弊,就像王安石信奉《周礼》,他是如何重蹈前人之错的。儘管医学被认为是小道,但却是仁爱之术,所以一定要真诚而认真地加以辩论」)。然后又说:「须知毒烈之气,留在何经而发何病,」但后面却不回答,不是故意要自相矛盾,其本义其实是要创造一种异气四变之理论而自成一派开山祖师。后人有谁知道这只是一场鬧剧呢?我哪裏是好辩之人啊?我是迫不得已才说的(眉批:这裏所说「毒烈之气,留在何经而发何病」原本是有道理的,但却是推翻了自己所言。由此可知「中而不即病,寒毒藏于肌肤」之说,在理论上是个大错。用此与王叔和对质,看他可以用什么来解释)。凡治疗伤寒病之大法,关键在于分清表裏。邪气未传入腑,就是在表,发汗即可。已传入腑,邪气在裏,攻下即可。至于温病,如果真的是寒毒藏于肌肤,延至春夏仍用辛温之药来解表,以为邪气会透过发汗而解,使得后世治疗温病之人,仍然执着于寒毒在于肌肤之表的说法,一味用发散药,不仅毫无益处,反而有害。而世间凶险之重病,其生死只在反掌之间者,全都是温病,而发于冬天之正伤寒病,只是极少数。但方书中却将温病与伤寒病混同立论,毫无分別。这完全是由于王叔和在整理《伤寒论》时,沒有将温病这一门编入其中,指其为「伏寒」、「异气」,错误地设立「温疟」、「风温」、「温毒」、「温疫」四种变化,将其插入《伤寒论》中混为一谈,这样一来,温病之证治体系不但遭到严重破坏,,甚至几乎被消亡。后之学者,从此就几乎无从追寻温病之源。对于这个问题上,我已经经过了长期的研究,加上临床治疗所得,确实看到了温病之根源(眉批:南山是可以被移平的,但对此事之看法则完全不可动摇)。伤寒是感受天地之常气,属于外感风寒之邪,自气分而传入血分。温病得之于天地之杂气,邪毒从内部进入,由血分发出气分(「常气」、「杂气」之说出自《温疫论》,「气分」、「血分」之说出自《伤寒缵论》,都是千古一来罕见的独特看法。根据这些说法来区分温病和伤寒病,以及区分温病和伤寒病之不同治疗,所以,这些说法并不是杜撰出来的)温病与伤寒病之间,实在是「风马牛不相及」。为甚么这样说呢?「常气」指的是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,即天地间四季交替运行之六气。「杂气」所指并非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气,而是天地间另一类气,例如在荒芜干旱或水涝之处而具杀厉之山岚瘴气等毒气。因此,「常气」所致之病在表浅而容易治癒,「杂气」所致之病在内深而难以治癒。(眉批:《温疫论》中「杂气」一词,开启了治疗温病无穷之治法,《伤寒缵论》中「血分」一词开启了治疗温病的无穷方论。乡间之人看到有发热、头痛、谵语等证时,大家惊恐地称其为「杂疾」,这就真合乎病源。经常遇到反而不能有所觉察的,是我们这些医生)。即使按照《序例》所说,「寒毒藏于肌肤,至春夏变为温病暑病」,那亦是寒毒自然转变成温病,变成暑病。这还是冬季之常气,亦犹如「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」之说,与杂气又有何关系呢?千古流传下来之错误,只因人们不了解「疵疠旱潦」之杂气是温病之源头,从而将其与伤寒病视为同一种病,而不加以区分地治疗。我所以不顾我见识疏陋,也要一点一点地将温病与伤寒病辨別清楚,它们各有病因,各有脉证,各有证候,各有治法,各有方论。这样可以让医家们早日采取应对策略,以免事到临头而焦头。 |
|
|
或问:《内经》曰「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」(眉批:引《经》一语道破)。馀曰:「冬伤于寒」,谓人当冬时受寒气也。「春必病温」,谓人到来春必病热也,亦犹《经》曰「人之伤于寒也,则为病热」云尔。东垣云:「其所以不病于冬,而病于春者,以寒水居卯之分,方得其权。」大寒之令復行于春,开发腠理。少阴不藏,辛苦之人,阳气外泄,谁为鼓舞?阴精内枯,谁为滋养?生化之源已绝,身之所存者热也。故《内经》又云:「冬不藏精,春必病温。」此水衰火旺,来春其病未有不发热者,于温病何与?温病者,疵疠之杂气,非冬来之常气也。肾虚人易为杂气所侵则有之,非谓「伤于寒则为温病」也。经何以不曰「温病」,而必曰「病温」?盖温者热之始,热者温之终也,岂诸家所谓「温病」者乎?特辩以正前人註释之谬(眉批:辩得精细)。 |
有人问:《内经》说「冬伤寒寒,春必病温」(眉批:引用《经》文将其一语道破)。我认为:「冬伤于寒」,是指人在冬天受到寒气。「春必病温」,是指人到了春天必然会患上热病,就像《经》书上亦曾说过,「人之伤于寒也,则为病热」。李东垣说:「人之所以不在冬季患病,而在春季患病的原因是,是因为寒水居于卯位时,与其正好相应」。大寒之气又在春天重现,腠理被开泄,少阴之气不藏,辛苦劳累之人则会阳气外泄,还怎么会有生发之机呢?阴精内枯,还怎么会有滋养之力呢?生化之源头已绝,人体所剩下的只有发热。因此,《内经》又说:「冬不藏精,春必病温」。这是冬天已经水亏火旺,到来年春季哪有不会发热的呢?这与温病有何关系?温病是由疵癖之杂气所引发,而不是冬季之常气。肾虚之人易受杂气侵袭,是存在的,并不是说「伤于寒则为温病」。《经》书为甚么不说「温病」,而非要说「病温」呢?因为温是热之开始,而热则是温之终结,这哪裏是各家所指的「温病」啊?特此辨析以纠正前人注释时所犯之错误(眉批:辨析得精细)。 |
|
|
1芸夫牧竖:即农夫牧童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读仲景书,一字一句都是精义,后人之千方万论,再不能出其范围,馀又何辩乎?盖仍本之仲景矣。《伤寒论》曰:「凡伤寒之为病,多从风寒得之(风属阳,寒属阴。然风送寒来,寒随风入,本为同气,故寒之浅者即为伤风,风之深者即为伤寒,故曰伤寒从风寒得之)。始因表中风寒,入裏则不消矣,未有温覆而当不消散者。」成氏註:「风寒初客于皮肤,便投汤药,温覆发散而当,则无不消散之邪。」此论伤寒治法也,其用药自是麻黄、桂枝、大小青龙一派(眉批:仍从《伤寒论》中看出,温病治法与伤寒不同,是读书得间处)。《伤寒论》曰:「凡治温病,可刺五十九穴。」成氏註:「以泻诸经之温热,谓泻诸阳之热逆,泻胸中之热,泻胃中之热,泻四肢之热,泻五藏之热也。」此论温病治法也,若用药当是白虎、泻心(眉批:泻心者,大黄黄连泻心汤也)、大柴胡、三承气一派。末又曰:「此以前是伤寒温病证候也。」详仲景两条治法,于伤寒则用温覆消散,于温病则用刺穴泻热,温病与伤寒异治判若冰炭。如此,信乎仲景治温病必別有方论(眉批:看仲景治法,温病与伤寒原是两门。惜经兵火之余,散亡不传耳。此段接上生下)。呜呼!歷年久远,兵燹散亡,王叔和指为「伏寒」,插入「异气」,后之名公,尊信附会,沿习耳闻,遂将温病为伤寒,混同论治。或以白虎、承气治伤寒,或以麻黄、桂枝治温病,或以为麻黄、桂枝今时难用,或以为温病春用麻黄、桂枝须加黄芩,夏用麻黄、桂枝须加石膏,或于温病知用白虎、泻心、承气,而不敢用麻黄、桂枝、青龙者。但昧于所以然之故,温病与伤寒异治处总未洞晰。惟王氏《溯洄》,着有伤寒立法考、温病热病说。其治法较若列眉,千年长夜忽遇灯炬,何幸如之!惜其不知温病中于杂气,而于严寒中而不即病,至春夏变为温暑之谬说一样煳涂。以为证治与伤寒异,病原与伤寒同,而未免小视轻忽之也。刘氏《直格》以伤寒为杂病,以温病为大病,特制双解散、凉隔散、三黄石膏汤,为治温病主方(眉批:所以然之故,乃得于杂气也,自血分发出气分也),其见高出千古,深得长沙不传之秘。惜其不知温病中于杂气,而于伤寒末传阴证,温病从无阴证之治法,无所发明。庸工不能解其理,不善用其方,而猥以寒凉摈斥之也。诸家混淆不清,而二公亦千虑之失也(眉批:王、刘二公,分辩温病与伤寒异治,是千古特识,但不知温病为杂气也,因此为辩明以补王、刘所未及。见得真,守得定,老吏断狱,铁案不移,二公当亦心折。二公唯不知温病为杂气,虽治分二门,其实不敢尽变叔和《序例》「伏寒」、「暴寒」之说,所以三黄石膏汤、双解散内仍用麻黄。披枝见根,溯流穷源,公于此乃点出金刚眼睛矣。本《平脉篇》中两次申明,不厌重复,正是婆心恳至处)。馀于此道中,抱膝长吟,细玩《伤寒论·平脉篇》曰:「清邪中上焦,浊邪中下焦,阴中于邪」等语,始翻然顿悟曰:此非伤寒外感常气所有事,乃杂气由口鼻入三焦,怫郁内炽,温病之所由来也。因此以辩温病与伤寒异,辩治温病与治伤寒异,为大关键。故多采王、刘二公之论,并《缵论》、《绪论》、《温疫论》、《尚论篇》,及诸前辈方论。但有一条一段不悖于是者,无不零星凑合,以发挥仲景「伤寒温覆消散」,「温病刺穴泻热」之意。或去其所太过,或补其所不及,或衍其所未畅,实多苦心云。 |
阅读张仲景之书,一字一句都包含着精义,后人纵有千万方论,亦不能超出仲景书之范围,我对此又有什么可以辩论呢?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本于仲景之书。《伤寒论》说:「凡是伤寒病多数是外感风寒邪气引起的(风属阳,寒属阴。然而风送寒气来,寒随风而入,实际上是一气,所以寒之浅者就是伤风,风之重者就是伤寒,所以说伤寒是外感风寒邪气引起的)。一开始为风寒袭表,邪气入裏则难以消散,而在表时只要温服药物并盖被发汗就能发散邪气。」成无己註:「风寒初次侵袭皮肤时,就让病者服汤药,温服而盖被进行发散得当,则沒有不消散之邪。」这是论伤寒病之治法,用药自然是麻黄汤、桂枝汤、大小青龙汤这一类(眉批:仍然从《伤寒论》中可以看出温病与伤寒病之治法不同,是通过读书而有所体会)。《伤寒论》说:「凡治温病,可刺五十九穴。」成无己註:「刺五十九穴用来泻诸经之温热,泻各阳邪之逆行,泻胸中之热,泻胃中之热,泻四肢之热,泻五脏之热。」这是论温病之治法,用药应该是白虎汤、泻心汤(眉批:泻心汤指的是大黄黄连泻心汤)、大柴胡汤、三承气汤等。《伤寒论》最后又说:「这之前所论是伤寒病和温病之证候。」仔细分析仲景两条治法,对伤寒病用「温盖发散」之法,而对温病则用「刺穴泻热」之法,可以温病和伤寒病治法之不同判若冰炭。如此可见,仲景对于温病之治疗必定別有方论(眉批:根据仲景之治法,温病和伤寒病本是两个不同的类別。只可惜经歷兵火战乱之后,散失不传。这承前启后之文)。呜呼!歷经多年战乱而亡失,王叔和将温病指为「伏寒」,又插入「异气」之说,后来之医家尊信附会而将其承传下来,将温病当作伤寒病并混同治疗。或用白虎汤、承气汤治伤寒病,或用麻黄汤、桂枝汤治温病,或以为现在难以用麻黄汤、桂枝汤,或以为治温病时春天用麻黄汤、桂枝汤加黄芩,夏天用麻黄汤、桂枝汤加石膏,或知道治温病要用白虎汤、泻心汤、承气汤,然而再不敢用麻黄汤、桂枝汤、青龙汤等。这都是只知道如何简单用方,而在理论上对于温病和伤寒病之种种不同还沒有完全明了。只有王履《医经溯洄集》一书,其中有伤寒病立法考和温病热病说二文。其治疗方法清清楚楚,就像在漫漫长夜中突然遇到明灯,是何其幸运!只可惜王氏不知道温病是由杂气所发,而对冬时受寒而不即病,至春夏而变为温暑之说一样煳涂不明。只是以为温病与伤寒病之证治是不同的,但其发病之因则是一样的,这未免将这个问题看轻了。刘完素《伤寒直格》将伤寒病视为杂病,将温病视为大病,并特別创制了双解散、凉隔散、三黄石膏汤等治疗温病之主方(眉批:之所以能如此,是由于温病得之于杂气,由血分发出气分),刘氏之见解独特而高于他人,深得仲景不传之秘。可惜他不知道温病伤于杂气,而对伤寒病末期有传变为阴证,温病则从来不会有阴证之治法沒有新的看法。一些庸医无法理解其中之理,亦不善于运用其方,而以其方过于寒凉之畏惧心态将其方弃而不用。医家们对于温病与伤寒病混淆不清,而这亦是王、刘两位医家之千虑一失(眉批:王履和刘完素二位名医,能分辨温病和伤寒病之不同治法,是长久以来少有的了不起看法,但却不知道温病属于杂气所致,因此,为了补充王履和刘完素所未及,才对此进行论证。这种认识看得真切,守得坚定,就像老练的法官审判案件一样,铁案不移,这两位名医应该会心服口服。两位名医只是不知道温病是杂气,虽然将治疗伤寒病与温病分为两门,实际上并不敢完全改变王叔和《序例》中「伏寒」、「暴寒」之说,所以在三黄石膏汤、双解散内仍然用麻黄。从枝叶看到根本,从流追溯到源,杨氏在此显示其火眼金睛。本于《平脉篇》中二次申明,不厌其烦地重复,真是苦口婆心诚恳到了极致)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通过深入研究《伤寒论·平脉篇》中所说「清邪中上焦,浊邪中下焦,阴中于邪」之文,我顿时领悟到,温病不属于伤寒外感常气所致之病,而是杂气从口鼻进入三焦,邪气拂郁于内,才是温病发生的真正原因。因此,通过辨別温病与伤寒病之不同来认识温病与伤寒病在治疗上之差异,成为一个关键问题。我经常采集王履和刘完素之观点,以及《伤寒缵论》、《伤寒绪论》、《温疫论》、《尚论篇》等前辈之方论,要有些观点与我的看法不矛盾,我都会零星之观点整合在一起,以发挥仲景「伤寒温覆消散」和「温病刺穴泻热」之心法。其中,可能做得太过,或者可能真的弥补了一些不足,或者发挥得尚未尽善,但确实是出于我一片苦心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凡邪所客,有「行邪」,有「伏邪」,故治法有难有易,取效有迟有速。「行邪」如冬月正伤寒,风寒为病,自外之内。有循经而传者,有越经而传者。有传一二经而止者,有传尽六经不罢者,有始终只在一经而不传者。有从阳经传阴经为热证者,亦有变为寒证者,有直中阴经为寒证者。正如行人经由某地,本无根蒂。因其漂浮之势,病形虽乱,若果在经,一汗而解。若果在胃,一下而愈。若果属寒,一于温补。若果传变无常,随经治之。有证可凭,药到便能获效。所谓「得天地之常气」,风寒外感,自气分传入血分者是也。先伏而后行者,温病也。无形无声者,难言矣。毒雾之来也无端,烟瘴之出也无时。温热熏蒸之恶秽,无穷无数,兼以饿殍在野,胔骼之掩埋不厚,甚有死尸连床,魄汗之淋漓自充。遂使一切不正之气,升降流行于上下之间,人在气交中无可逃避。虽童男室女,以无漏之体,富贵丰亨。以幽闲之志,且不能不共相残染,而辛苦之人可知矣,而贫乏困顿之人又岂顾问哉(眉批:杂气侵人,无论贫富强弱。说得淋漓洞快,令人目开心朗)?语云「大兵之后,必有大荒,大荒之后,必有大疫」,此天地之气数也,谁能外之?疵疠旱潦之灾,禽兽往往不免,而况人乎?所谓「得天地之杂气」,邪热内郁,由血分发出气分者是也。当其初病之时,不唯不能即疗其病,而病势日日加重,病家见病反增,即欲更医。医家不解其故,亦自惊疑,竟不知先时蕴蓄,邪微则病微,邪甚则病甚。病之轻重非关于医,人之死生全赖药石。故谚有之曰:「伤寒莫治头,劳病莫治尾。」若果是伤寒,初受肌表,不过浮邪在经,一汗可解,何难之有?不知盖指温病而言也。要其所以难者,总因古今医家,积习相沿,俱以温病为伤寒,俱以伤寒方治温病,致令温魂疫魄含冤地下。诚能分析明白,看成两样脉证,两样治法,识得常气杂气,表裏寒热,再详气分血分,内外轻重,自迎刃而解,何至杀人耶?虽曰温病怪证奇出,如飚举蜂涌,势不可遏。其实不过专主上中下焦,毒火深重,非若伤寒外感,传变无常。用药且无多方,见效捷如影响,按法治之,自无殒命之理。至于死而復甦,病后调理,实实虚虚之间,用药却宜斟酌,妙算不能预定,凡此但可为知者道也。若夫久病枯藁,酒色耗竭,耆老风烛,已入四损不可正治之条,又不可同年而语。 |
凡是外邪伤人,有「行邪」,有「伏邪」,因此治法有难有易,取效有迟有速。「行邪」如冬月之正伤寒,风寒外感而病,邪气自外传入于内,有循经传,有越经传。有传一两经而止,有传变六经而不止,有始终只在一经而不传。有从阳经传至阴经变为热证,亦有变为寒证,有直中阴经为寒证。就像行人经过某地,本来沒有原由。只因病情漂浮不定,病情虽然杂乱,但如果邪气在经,一经发汗则解。如果邪在胃中,一经攻下则癒。如果属于寒邪,就用温补之法。如果传变无常,就随经进行治疗。只要有证可辨,药到就能病除。所谓「得天地之常气」,就是风寒外感,由气分病传入血分。而先潜伏后发病,就是温病。温病无形无声,难以用言语描述。毒雾无端地来临,瘴气不时出现。温热熏蒸所致之恶秽邪气,无处不在,加上饥殍在野,尸体掩埋不深,甚至尸体就在床上,腐烂之气充室。因而使得一切不正之气在天地上下流行,人在天地之间则无处可避。即使是尚未洩精之童男童女,亦同样会因此而病。即使是志向安闲之人亦无法避免不相互传染,更何况那些辛苦劳作之人,就可想而知了,哪裏还用说那些贫乏困顿之人呢(眉批:雑气侵犯人,是不分贫富强弱的。这句话说得淋漓明快,令人一清二楚)?谚语说:「战争之后,必然有大飢荒,大飢荒之后,必定出现大疫情。」这是天地间必然会发生的事,有谁能例外呢?疵疠旱潦之气所带来之灾难,禽兽都无法倖免,更何况人呢?所谓「得天地之杂气」,邪热内郁,病由血分外出气分。在发病初期,不仅不能立即治好此病,而且病势日益加重,病家见病情反而加重,便想再更换医者。医生不明白为何治不好,自己都感到惊疑,竟然不知道先前只是邪气酝郁蓄积,邪微则病微,邪甚则病甚。疾病之轻重与医生无关,但人之生死则完全依赖药物。所以谚语说:「治伤寒病不治其始发之病,而治劳病则不治其终结之病。」如果确实是伤寒病,病初邪在肌表,不过是浮邪在经络,一经发汗则解,有何难度?不知道治不好之病是温病。温病之所以难治,主要是因为古今医家都习惯将温病视为伤寒病,都用伤寒方治疗温病,导致温病被误治之人含冤而死。如果能够将温病与伤寒病分辨清楚,两种疾病,两种脉证,两种治法,明白常气和杂气所致表裏寒热之不同,再详辨病在气分和血分,内外轻重之证自然能够迎刃而解,怎么会由医病变成杀人呢?虽然说温病之怪证很多,如暴风及蜂涌般势不可遏。但实际上则以上中下三焦之毒火深重为主,而不像伤寒病外感邪气后变化无常。而且治疗温病用药不多,也沒有那么多方,见效迅速,只要依法治疗,自然不会引致丧命。至于转危为安之人,其病后调理,虚虚实实之间用药都需要斟酌,无法一一事先设定,这些方面只能向明白温病之人来说。对于那些久病枯藁,酒色耗竭,风烛残年,已经属于「四损」不可正治者,则不能相提并论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或曰:子辩温病与伤寒,有云壤之別。今用白虎、泻心、承气、抵当,皆伤寒方也。既同其方,必同其证,子何言之异也?馀曰:伤寒初起必有感冒之因,冬月烈风严寒,虽属天地之常气,但人或单衣风露,或强力入水,或临风脱衣,或当檐沐浴,或道路沖寒,自觉肌肉粟起,既而四肢拘急、头痛发热、恶寒恶风。脉缓有汗为中风,脉紧无汗为伤寒。或失治,或误治,以致变证蜂起。温病初起,原无感冒之因,天地之杂气,无形无声,气交流行,由口鼻入三焦,人自不觉耳。不比风寒感人,一着即病。及其郁久而发也,忽觉凛凛,以后但热而不恶寒,或因飢饱劳碌,焦思气郁,触动其邪,是促其发也。不因所触,内之郁热自发者居多。伤寒之邪,自外传内;温病之邪,由内达外。伤寒多表证,初病发热头痛,末即口燥咽干。温病皆裏证,一发即口燥咽干,未尝不发热头痛。伤寒外邪,一汗而解。温病伏邪,虽汗不解,病且加重。伤寒解以发汗,温病解以战汗。伤寒汗解在前,温病汗解在后。鲜薄荷连根捣,取自然汁服,能散一切风毒。伤寒投剂,可使立汗。温病下后,裏清表透,不汗自愈,终有得汗而解者。伤寒感邪在经,以经传经。温病伏邪在内,内溢于经。伤寒感发甚暴,温病多有淹缠,三五七日忽然加重,亦有发之甚暴者。伤寒不传染于人,温病多传染于人。伤寒多感太阳,温病多起阳明。伤寒以发表为先,温病以清裏为主。各有证候,种种不同。其所同者,伤寒温病皆致胃实,故用白虎、承气等方清热导滞。后一节治法亦无大异,不得谓裏证同而表证亦同耳。 |
有人说:你认为伤寒病与温病有天壤之別,而现在所用之白虎汤、泻心汤、承气汤、抵当汤等方皆是伤寒方剂。既然使用相同之方剂,必然针对相同之证候,你为何会说两者是不同的呢?我回答説:伤寒初起必然有感受风寒邪气之病因,冬天寒风刺骨,虽然属于天地之常气,但人可能穿着单薄的衣物暴露在寒气中,或者强行下水,或者当风脱去衣服,或者在屋檐下沐浴,或者在路上受寒,然后就感到身上起鸡皮疙瘩,接着就四肢拘急、头痛、发热、恶寒、恶风。脉缓有汗者为中风证,脉紧无汗者为伤寒证。或因失治,或因误治,以致出现各种变证。而温病初起时,本来沒有感受外邪,只是天地之杂气,无形无声在天地间流行,通过口鼻进入三焦,人自然不会觉察到。雑气不像风寒邪气伤人,犯人即发病。雑气郁久之后才发作,忽然感到身寒,之后只有发热而不恶寒,或者因为飢饱劳累、焦虑忧思等触动邪气而导致雑气发作。沒有因外有所触,而由在裏之郁热自然发作者居多。伤寒之邪是自外入内,温病之邪则是由内达外。伤寒多表证,初起时发热头痛,不会当时口干咽干。温病全为裏证,一发作就口干咽干,但亦会发热头痛。伤寒病之外邪,一经发汗则解。温病之邪气,即使发汗也不解,反而会使病情加重。伤寒病通过发汗而解,温病则通过战汗而解。伤寒病在早期时通过发汗而解,温病则在晚期时通过战汗而解。用新鲜薄荷连根捣碎,取其汁液服用,能驱散一切风毒邪气。伤寒使用药汤,可以立即使病者出汗。温病经过攻下后,内邪已清,表气通畅,不需发汗自然就癒,不过亦有最终还是会出汗而解者。伤寒病邪犯于经,在经脉之间相互传变。温病之伏邪在内,从内扩散至经脉。伤寒病感邪后发病非常迅速,温病则多有潜伏,过三、五、七天后突然加重,但亦有暴发者。伤寒病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,温病则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。伤寒感邪后常始于太阳经,温病则多发生在阳明经。伤寒病以发汗解表为先,温病则以清除裏热为先。两种病各有其种种不同之证候,所共同之处在于都导致胃家实,因此都用白虎汤、承气汤等方以清热通滞。其后续之治法亦沒有太大的不同,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两种病之胃家实相同,就等于两病之表证亦相同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客有过而问之者曰:闻子着《寒温条辩》,将发明伤寒乎?抑发明温病也?特念无论伤寒温病,未有不发于寒热者。先贤之治法,有以为热者,有以为寒者,有以为寒热之错出者,此为治病大纲领,盍为我条分而辩论焉?馀曰:愿受教。客曰:《内经》云:「热病者,伤寒之类也。人之伤于寒也,则为病热。未入于府者,可汗而已;已入于府者,可下而已。三阳三阴,五藏六府皆受病,荣卫不行,脏腑不通,则死矣。」又曰:「其未满三日者,可汗而已;其满三日者,可下而已」。《内经》直言伤寒为热,而不言其有寒。仲景《伤寒论》垂一百一十三方,用桂、附、人参者八十有奇。仲景治法与《内经》不同,其故何也?馀曰:上古之世,恬淡浑穆,精神内守。即有伤寒,一清热而痊可,此《内经》道其常也。世不古若,人非昔比。以病有浅深,则治有轻重。气禀日趋于浇薄,故有郁热而兼有虚寒,此仲景尽其变也(眉批:道常尽变,说尽古今病势人情)。客又曰:伤寒以发表为第一义,然麻黄、桂枝、大青龙每苦于热而难用。轻用则有狂躁、斑黄、衂血、亡阳之失,致成热毒坏病,故河间自制双解散、凉膈散、三黄石膏汤(眉批:双解、凉膈、三黄石膏、六一顺气、大柴胡五方,有治伤寒温病之不同处,观药方辩自知。解毒承气汤,即大承气汤合黄连解毒汤;加白殭蚕、蝉蜕,去栀、柏,即泻心承气汤;加栝楼、半夏,即陷胸承气汤)。若麻黄、桂枝、大青龙果不宜用,仲景何以列于一百一十三方之首乎?致使学者视仲景书,欲伏焉而不敢决,欲弃焉而莫之外。夫仲景为医家立法不祧之祖,而其方难用,其故何也?馀曰:伤寒以病则寒,以时则寒,其用之固宜。若用于温病,诚不免狂躁、斑黄、衂血、亡阳之失矣。辛温发散之药,仲景盖为冬月触冒风寒之常气而发之伤寒设,不为感受天地疵疠旱潦之杂气而发之温病设。仲景治温病必別有方论,今不见者,其亡之也。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,功莫大矣。但惜其以自己之说,杂于仲景所言之中,使玉石不分耳。温病与伤寒异治处,惟刘河间、王安道始倡其说,兼馀屡验得凶厉大病,死生在数日间者,惟温病为然。而发于冬月之正伤寒者,百不一出,此河间所制双解、凉膈、三黄石膏,清泻内热之所以可用,而仲景麻黄、桂枝、大青龙,正发汗者之所以不可用也。盖冬月触冒风寒之常气而病,谓之伤寒。四时触受疵疠之杂气而病,谓之温病。由其根源之不一,故脉证不能相同,治法不可相混耳(眉批:此段辩温病与伤寒之异,辩治温病与治伤寒之异,坦白明亮,毫无矇混,而笔力足以达之)。客又曰:人有伤寒初病,直中三阴,其为寒证无疑矣。又有初病三阳,本是热证,传至三阴,裏实可下,止该用承气、抵当,乃间有寒证可温可补,又用理中、四逆,其故何也?馀曰:以初本是热证,或久病枯竭,或暴感风寒,或饮食生冷,或过为寒凉之药所攻伐,遂变成阴证。所云「害热未已,寒证復起。始为热中,末传寒中」是也。且人之虚而未甚者,胃气尚能与邪搏而为实热之证。若虚之甚者,亡阳于外,亡阴于内,上而津脱,下而液脱,不能胜其邪之伤,因之下陷,而裏寒之证作矣(眉批:伤寒直中三阴是寒证,若本是热证,传至三阴热证变为寒证者,王、刘亦未言及。此足补之)。热极生寒,其证多危,以气血之虚脱也。客又曰:寒热互乘,虚实错出,既闻命矣。子之治疗,果何以得其宜,条辩之说,可闻否乎?馀曰:证治多端,难以言喻。伤寒自表传裏,裏证皆表证侵入于内也。温病由裏达表,表证即裏证浮越于外也(眉批:「侵入」、「浮越」四字,令人咀嚼不尽)。大抵病在表证,有可用麻黄、桂枝、葛根辛温发汗者,伤寒是也。有可用神解、清化、升降、芳香、辛凉、清热者,温病是也。在半表半裏证,有可用小柴胡加减和解者,伤寒是也;有可用增损大柴胡、增损三黄石膏汤内外攻发者,温病是也。在裏证,有可用凉膈、承气咸寒攻伐者,温病与伤寒大略同。有可用理阴、补阴、温中、补中调之养之者,温病与伤寒大略同。但温病无阴证,宜温补者,即所云「四损」,不可正治也。若夫伤寒直中三阴之真寒证,不过理中、四逆、附子、白通,一于温补之而已。至于四时交错,六气不节,以致霍乱、疟痢、吐泻、咳嗽、风温、暑温、湿温、秋温、冬温等病。感时行之气而变者,或热,或寒,或寒热错出,又当观其何时何气,参酌伤寒温病之法,以意消息而治之(眉批:补出寒证治法,又补出时气病治法,何等緻密)。此方治之宜,大略如此。而变证之异,则有言不能传者,能知意在言表,则知所未言者矣。客又曰:子之治疗,诚无可易矣。第前辈诸名家,皆以为温暑之病本于伤寒而得之,而子独辩温病与伤寒根源异,治法异,行邪伏邪异,证候异,六经脉证异,并与时气之病异,得勿嫌于违古乎?馀曰:吾人立法立言,特患不合于理,无济于世耳。果能有合于理,有济于世,虽违之庸何伤?客唯唯而退。因櫽括其说曰:寒热为治病大纲领辩,尚祈临病之工,务须辩明的确。或为伤寒,或为温病,再谛审其或属热,或属寒,或属寒热错出,必洞悉于胸中,然后诊脉定方。断不可偏执己见,亦不可偏信一家之谬说,庶不至于差错也。 |
有前来拜访的客人问:听闻你撰写《寒温条辩》,将会发挥伤寒病理论?抑或是发挥温病呢?只是想到,无论伤寒病还是温病,沒有不是因为寒热之邪而发。前人之治法,有的认为属热,有认为属寒,有认为属寒热错杂,并以此为治病之大纲领,为什么不为我逐条分辨呢?我说:愿意接受指教。客人说:《内经》说「热病者,伤寒之类也。人之伤于寒也,则为病热。未入于腑者,可汗而已;已入于腑者,可下而已。三阳三阴,五脏六腑皆受病,荣卫不行,脏腑不通,则死矣。」又说:「其未满三日者,可汗而已;其满三日者,可下而已。」《内经》中直言伤寒病为热病,而不说为寒病。仲景《伤寒论》中一百一十三方,用到桂枝、附子、人参之方有八十多条。仲景之治法与《内经》的不同,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呢?我说:上古之人,生活恬淡,质朴淳和,能够精神内守。一旦患上伤寒病,一经清热即可痊癒,这是《内经》所说的一般情况。世事变更,今非昔比。因为疾病有浅深,所以治法有轻重。人所禀受之气日渐贫薄,所以有郁热而会兼有虚寒,所以仲景根据其变化而改变治法(眉批:世道经常会完全改变,此句完全说出了古今病势与人情之变化)。客人又说:伤寒病最重视发汗解表,但是麻黄汤、桂枝汤、大青龙汤每因于其性热而难以运用,轻一点的话可造成狂躁、发斑、黄疽、出血、亡阳等失误,引致热毒一类坏病。因此,刘河间自制双解散、凉膈散、三黄石膏汤(眉批:双解散、凉膈散、三黄石膏汤、六一顺气汤、大柴胡汤五方,可治伤寒病、温病之不同阶段,观其方论自能辨清。解毒承气汤,即大承气汤合黄连解毒汤;加白殭蚕、蝉蜕,去栀子、黄柏,即是泻心承气汤;加栝蒌、半夏,即陷胸承气汤)。如果麻黄汤、桂枝汤、大青龙汤真的不适宜用,仲景为何将其列于一百一十三方之首呢?致使后学之人读仲景书时,想跟从其意但又不敢运用,想抛弃它但又沒有其他可替代之书。仲景是后世医家立法治病之始祖,但其方如此难用,原因何在?我说:伤寒病是因寒而病,所病之时亦在寒冷之季,所以其用当然适合。如果用来治温病,确实难免会导致狂躁、发斑、黄疽、出血、亡阳等失误。辛温发散之药,是仲景为冬月触冒了风寒之常气所引发之伤寒病而设的,不是为了感受天地杂气所发之温病而设。仲景治温病必定另有方药论述,现在不见了,是因为亡轶了。王叔和搜集仲景以前散落之论书,其功劳十分大。但可惜他将自己之观点掺杂在仲景书中,致使玉石不分。能提出温病与伤寒病之不同治疗,只有从刘河间、王安道才开始,加上在我屡屡的治疗经验当中,发现只有温病才是最多见的凶险大病,生死存亡只在数天之间。而这些情况对于发生于冬月之正伤寒病来说是极为罕有。这就是为什么刘河间所制之双解散、凉膈散、三黄石膏汤,能清泻内热而经常可以被用到,但仲景真正用来发汗之麻黄汤、桂枝汤、大青龙汤却不可以用。冬天触冒风寒之常气所发之病为伤寒病。四时触冒感受疵厉之杂气所发之病为温病。由于两病之根源不一样,所以脉证不同,治法亦不能互相混淆(眉批:此段辨別温病与伤寒病之不同,及其治疗上之不同,坦白明亮,毫不含煳,文笔之力足以反映出来)。客人又说:有人初患伤寒病,直中三阴,这无疑是寒证了。又有初病在三阳,本是热证,传至三阴,有裏实可下之证,只该用承气汤、抵当汤,但其间又有可温可补之寒证而用用理中汤、四逆汤,原因何在呢?我说:由于初病时本是热证,或者久病以致阴阳枯竭,或突然感受风寒邪气,或饮食生冷,或过度使用寒凉药物攻伐,因而热证变成了阴证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「害热未已,寒证復起。始为热中,末传寒中」。而且人之虚弱尚未至于严重时,胃气尚能与邪气抗争则能成为实热之证。如果虚弱已很严重,阳亡于外,阴亡于内,上部津脱,下部液脱,不能承受邪气所伤,因此邪气下陷,就会发生裏寒之证(眉批:伤寒病直中三阴是寒证,如果本来是热证,传至三阴后热证则变为寒证,王安道、刘完素都沒有提到。这裏对此足以补充)。热极生寒,病证多属危重,因为气血已经虚脱。客人又说:寒热互呈,虚实错雑,已听您说过了。您可否逐一说一下对此如何进行治疗?我说:临床上证候治法多端,难以简单用言语说明。伤寒病自表传入裏,裏证皆是从表证侵入于内。温病由裏透达于表,表证实际是裏证浮越于外(眉批:「侵入」、「浮越」四字,令人回味无穷)。大概病在表,可用麻黄汤、桂枝汤、葛根汤辛温发汗之法的,是伤寒病。有用神解散、清化饮、升降散之芳香、辛凉、清热方法的,是温病。属于半表半裏证,可用小柴胡汤加减进行和解者,是伤寒病;有可用增损大柴胡汤、增损三黄石膏汤进行内攻外发者,则是温病。至于裏证,可用凉膈散、承气汤之咸寒攻伐者,温病与伤寒病大致相同。有可用理阴煎、补阴益气煎加以温中、补中进行调养者,温病与伤寒病亦大致相同。但是温病无阴证,如果有当用温补之法者,即所谓「四损」,是难以治疗的。对于伤寒病直中三阴之真寒证,不过用理中汤、四逆汤、附子汤、白通汤,一经温补就可以了。至于四时交错,六气不节所引致之霍乱、疟痢、吐泻、咳嗽、风温、暑温、湿温、秋温、冬温等病,感受时行之气而产生之病变,或寒或热,或寒热错杂,又应当观察当时是何时何气,仔细斟酌治疗伤寒病与温病之法,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灵活调治(眉批:补充了寒证治法,又补充了时气病治法,多么严谨啊)。有关温病与伤寒病之方药治疗,大概就是如此。而变证之种种不同,则有不能言传者,能知道有些已经说过的,应该可以推知所未言及之处。客人又说:你所说的治疗诚然无法替代。只是以前之名家,皆以为温病及暑病原本由于伤于寒而得,而独惟你将温病与伤寒病的根源、治法、行邪伏邪、证候、六经之脉证分辨开来,并将其与时气所致之病分开来,不怕被人说是有违古制吗?我说:我们建立理论,着书立说,只会担心不合于理,对世人有无益。如果所说的合理,有益于世,虽然违背古制,那又有什么损害?客人恭敬地离去了。在此将前述进行总结:寒热辨证是治病之大纲,希望临证之医对此务必有准确之辨证。或为伤寒,或为温病,一定要明确判断其属热属寒,或属寒热错雑,必须心中一清二楚,然后才能诊脉用方。一定不可以偏执己见,亦不可以偏信一家之谬说,这才不至于酿成差错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伤寒,冬月感冒风寒之常气而发之病名也。温病,四时触受天地疵疠旱潦之杂气而发之病名也。根源歧出,枝分派別,病态之异,判若霄壤。窃验得凶厉大病,死生人在数日间者,尽属温病,而发于正伤寒者,未尝多见(眉批:温病与伤寒异处,不厌重复言之,正是婆心恳切处。从此得解,是作书根本处)。萧万舆《轩歧救正》曰:「其值严冬得正伤寒者,二十年来,于千人中仅见两人,故伤寒实非大病,而温病方为大病也。」从来伤寒诸籍,能辩温病与伤寒之异治者,止见刘河间、玉安道两公。而病原之所以异处,亦未道出汁浆。馀宗其说而阐发之,着为《寒温条辩》。若论裏证,或清或攻,或消或补,后一节治法,温病与伤寒虽曰不同,亦无大异。唯初病解表前一节治法,大有大渊之別(眉批:前一节治法大异,此论发前人未发之奇)。盖伤寒感冒风寒之常气,自外而传于内,又在冬月,非辛温之药,何以开腠理而逐寒邪,此麻黄、桂枝、大青龙之所以可用也。若温病得于天地之杂气,怫?在裏,由内而达于外(眉批:伤寒得于常气,温病得于杂气,本又可《温疫论》,王、刘亦未言及。论温病无外感,而内之郁?自发,以补王、刘所未及),故不恶寒而作渴。此内之郁?为重,外感为轻。兼有无外感,而内之郁?自发者,又多发在春夏,若用辛温解表,是为抱薪投火,轻者必重,重者必死。惟用辛凉苦寒,如升降、双解之剂,以开导其裏?,裏?除而表证自解矣。亦有先见表证而后见裏证者(眉批:论温病证有先见表而后见裏者,以补王刘所未及),盖怫?自内达外,?郁腠理之时,若不用辛凉解散,则?邪不得外泄,遂还裏而成可攻之证,非如伤寒从表而传裏也。病之轻者,神解散、清化汤之类;病之重者,芳香饮、加味凉隔散之类。如升降散、增损双解散,尤为对证之药。故伤寒不见裏证,一发汗而外邪即解;温病虽有表证,一发汗而内邪愈炽。此麻黄、桂枝、大青龙,后人用以治伤寒,未有不生者,用以治温病,未有不死者。此前一节治法,所谓大有天渊之別也(眉批:伤寒发汗,温病不发汗,此着治法高出常格,异处即在此)。举世不醒,误人甚众,故特表而出之,以告天下之治温病而等于伤寒者。又温病要得主脑,譬如温气充心,心经透出邪火,横行嫁祸,乘其暇隙亏损之处,现出无穷怪状,令人无处下手。要其用药,只在泻心经之邪火为君,而余邪自退。每见人有肾元素虚,或适逢淫欲,一值温病暴发,邪陷下焦,气道不施,以致便闭腹胀,至夜发?,以导赤、五苓全然不效。一投升降、双解而小便如注。又一隅之亏,邪乘宿损,如头风痛、腰腿痛、心痛、腹痛、痰火喘嗽、吐血便血、崩带淋沥之类,皆可作如是观。大抵邪行如水,唯注者受之。一着温病,旧病必发,治法当先主温病。温邪退,而旧日之病不治自愈矣。不得主脑,徒治旧病,不唯无益,而坏病更烈于伤寒也(眉批:此论发前人所未发,医家病家多为旧病所误)。若「四损」之人,又非一隅之亏者可比。伤寒要辩疑似,有如狂而似发狂者,有蓄血发黄而似湿发黄者,有短气而似发喘者,有痞满而似结胸者,有并病而似合病者,有少阴发?而似太阳发?者,有太阳病脉沉而似少阴者。太阳少阴俱是发?、脉沉细,但以头痛为太阳,头不痛为少阴辩之。头绪多端,务须辩明,如法治疗。若得汗、吐、下合度,温、清、攻适宜,可收十全之功,不至传变而成坏病矣(眉批:此篇论温病伤寒治法,各见精妙,而其文亦有笔有法,古致错落,忽止忽起,正如断岭连峰出沒隐现,一望无际,彷彿张中丞后传。——)。《伤寒论》中,共计坏病人十有六,故伤寒本无多病,俱是辩证不明,错误所致。如太阳始病,当以汗解。如当汗不汗,则郁?内迫而传经。如发汗太过,则经虚风袭而成痉。如不当汗而汗,则迫血妄行而成衂。大便不可轻动,动早为犯禁。当汗误下,则引邪入裏,而为结胸痞气,协?下利。当下误汗,则为亡阳,下厥上竭谵语。小便不可轻利,轻利为犯禁。盖自汗而渴,为湿?内盛,故宜利。如不当利而利,必耗膀胱津液而成燥血发狂。如当利不利,必就阳明燥火而成蓄血发黄(眉批:治伤寒大法,不过所云云者,妙在要认的证,才下的药,不然则纸上谈兵矣)。若夫内伤类伤寒者,用药一差,死生立判。盖内伤头痛,时痛时止;外感头痛,日夜不休。内伤之虚火上炎,时时鬧?,但时发时止,而夜甚于昼;外感之发?,非传裏则昼夜无休息。凡若此等,俱要明辩于胸中,然后察色辩声,详证诊脉,再定方制剂,庶不至误伤人命耳(眉批:补出内伤类伤寒来,治法与伤寒自是不同)。 |
伤寒病,是冬月感受触冒风寒之常气所发之病名。温病,四时触冒天地疵疠旱潦之杂气所发之病名。两者根源之不同,疾病发展过程之不同,病情证候之不同,有如天地之不同。我所经歷过病情凶险之大病,人之生死只数日之间的,都是属于温病,而发于真正伤寒病者,则未有经常遇见(眉批:将温病与伤寒病不同之处不厌其烦地重复,真是苦口婆心恳切之处。从今之后对此能够明白,是本书最根本之处)。萧万舆《轩岐救正》说:「那些正值严冬所得之真正伤寒病,二十年来,于千人中仅仅见到两人,因此伤寒病实在并非大病,而温病才是大病。」从来论述伤寒病之书籍,能够分辨温病及伤寒病的不同治疗,只有刘河间和王安道两位先生。但是当中对于病源之不同,仍未能说出来。我根据他们的学说对此加以阐发,写成《寒温条辩》一书。如果论及裏证,或清或攻,或消或补,后面一步谈温病与伤寒病之治法,虽然有所不同,但亦无很大差异。唯独前面一步论初病时解表之法,则有天渊之別(眉批:前一步有关病初时治法之大异,这种说法前所未有)。因为伤寒病是感受风寒之常气,自外传经于内,又是在冬月期间发病,如果不用辛温之药,怎么能开发腠理而驱逐寒邪?这就是为什么可用麻黄汤、桂枝汤、大青龙汤之道理。而温病是得于天地之杂气,怫热在裏,由内而达于外(眉批:伤寒病是感受常气,温病是感受杂气,这说法是根据吴又可《温疫论》,而王安道、刘完素都沒有提到这一点。在此论温病是不是感受感外邪,而是在内之郁?自发,是补充王安道、刘完素所沒有提到的),因此不恶寒而口渴。这是以在内之郁热为重,而外感为轻,加上沒有外感,只是在内之郁热自发之情况多发生在春夏季,如果此时用辛温解表之法治疗,就犹如抱着柴枝投向烈火,病轻者必然会转重,病重者就会死。只有用升降散、双解散辛凉苦寒之剂以开导其裏热,裏热除则表证能自然解除。也有一些先见表证,而后见裏证者(眉批:此处论温病有先见表证而后见裏证者,以补充王安道、刘完素所沒有提到的)。因为怫热自内达外,热郁腠理之时,如果不用辛凉解散,则热邪不能得以外泄,热邪就会还入于裏而成可攻之证,并不像伤寒病由表而传于裏。病轻的,用神解散、清化汤之类;病重的,用芳香饮、加味凉膈散之类。而象升降散、增损双解散,则更是对证之方。因此,伤寒病未见裏证时,一经发汗外邪即能解散;温病虽然有表证,一发汗则内邪愈加炽盛。这就是为什么后人用麻黄汤、桂枝汤、大青龙汤来治伤寒病,未有不愈者,而用此来治温病,则未有不死者。这就是前面一步论初病时解表之法,温病与伤寒病有天渊之別(眉批:伤寒病要发汗,温病则不能发汗,这种治法高出常规,不同之处即在于此)。世人在此不能醒悟,贻害很多人,因此要特意对此加以宣扬,以警示天下将温病等同于伤寒病治疗之人。又,治认识温病要认识其关键之处,例如温热之邪充斥于心,从心经透出之邪火会横行于各处引发各种病证,只要人身体内亏损之,就会出现各种奇怪病证,令人无从下手。而用药之关键所在,只要以清泻心经之邪火为主,其余各处之邪会自然退却。常常见到有人肾气素虚,或适逢淫慾,一遇上温病突然发生,邪气陷于下焦,气道不为所用,以致便闭腹胀,至夜则发热,用导赤散、五苓散全都无效。一用升降散、双解散,即小便通利如注。又可能是某处亏损,邪气便会乘机入其虚损之处,如头风痛、腰腿痛、心痛、腹痛、痰火喘嗽、吐血便血、崩带淋沥之类,都可以如此来理解。大概邪气就如同水流一般,只要有可流注之处就会受到邪气。一患上温病,旧病必然随之发作,治法上当先主治温病。只要温邪退却,而旧日之病就能不治而自癒。认识不到治病关键之处,只是医治旧病,不但无益,而其坏病会比伤寒病更勐烈(眉批:此处论述了前人所未有提及者,医家病家经常因为只顾旧病而误治)。如果是「四损」之人,又非一处亏损之人可比。伤寒病要辨別疑似之处,有如狂而似发狂,有畜血所致发黄而似湿热所致发黄,有短气而似气喘,有痞满而似结胸,有并病而似合病,有少阴发热而似太阳发热,有太阳病脉沉而似少阴病。太阳病与少阴病俱是发热、脉沉细,但以头痛为太阳病,头不痛为少阴病去分辨。头绪多端,务必要辨证明确,依法治疗。如果汗、吐、下之法及温、清、攻之法能适宜地运用,可收到十全之功,不至于传变而成为坏病(眉批:本篇论述温病和伤寒病之治法,处处展现其精妙,而其文笔亦有章法,错落有致,忽止忽起,就像连绵起伏之山峦出沒隐现,一望无际,仿佛是张中丞之传人)。《伤寒论》中,总计有十六条论述坏病,所以伤寒病本身并无很多病变,都是因为辨证不明,医者误治所致。如太阳病刚开始时,当用汗法,如果当用汗法而不用汗法,则郁热内迫导致传经。如发汗太过,则经气虚弱而受风袭则成痉病。如不当发汗而用汗法,则迫血妄行而成衄血。不可以轻易攻下大便,过早攻下就是犯了禁忌。应当发汗而误用下法,则会引邪入裏,导致结胸、痞气,协热下利等。应当攻下而误用发汗,则成亡阳之变,出现下厥上竭而谵语。不可以轻易利小便,轻易利小便就是犯了禁忌。因为自汗而口渴,为湿热内盛,所以可以利小便。如果不当利小便而利之,必然耗损膀胱津液而造成为血燥发狂。如果当利小便而不利小便,必然与阳明燥热相合而导致蓄血发黄(眉批:治伤寒大原则,只不过就这样说说而已。最重要是辨证准确,用药准确,不然就成了纸上谈兵)。如果是内伤病而类伤寒病者,用药稍有差池,生死立判。内伤病之头痛是时痛时止,而外感病之头痛则日夜不休。内伤病之虚火上炎,不时发热,但时发时止,而且夜晚甚于白昼。外感病之发热,如过尚未传裏,则昼夜不休。凡类似这样的情况,都要在心中明辨,然后观察形色,辨別声音,详细了解病者之脉证,然后再制定方药,这样才不至于误伤性命(眉批:这裏补充了内伤病而类伤寒病者,治法与伤寒病自然是不同的)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春温,夏暑,秋凉,冬寒,此四时错行之序,即「非其时有其气」,亦属天地之常,而杂气非其类也。杂气者,非温非暑,非凉非寒,乃天地间另为一种疵疠旱潦之毒气,多起于兵荒之岁,乐岁亦有之。在方隅有盛衰,在四季有多寡,此温病之所由来也。叔和《序例》有云:「春应温而反大寒,夏应暑而反大凉,秋应凉而反大?,冬应寒而反大温,非其时有其气。一岁之中,长幼之病多相似者,此则时行之气也」(旁批:慄山曰:馀读《绪论》「冬月温气乘虚人裏,遂至合病」,而悟冬温与风温、暑温、湿温、秋温,并疟痢、咳呕、霍乱等证,皆时行之气病也,正如叔和所云。而杂气非其种耳,与温病何干)。观于此言,嘴裏说得是「时气」,心裏却当作「温病」,由是而天下后世之言温病者,胥准诸此。而温病之实失焉矣,而时气病之实亦失焉矣。总缘人不知疵疠旱潦之杂气而为温病,抑不知时行之气,宜?而冷,宜冷而?,虽损益于其间,及其所感之病,岂能外乎四时之本气?(眉批:伤寒、温病、时气,方书皆混而一之,得此辩別明白,自可免人错误,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者也)假令春分后,天气应煖,偶因风雨交集,不能温煖而反大寒,所感之病,轻为感冐,重为伤寒。但春寒之气,终不若隆冬杀厉之气,投剂不无轻重之分,此为应至而不至。如秋分后,适多风雨,暴寒之气先至,所感之病,大约与春寒彷彿。深秋之寒,亦不若隆冬杀厉之气为重,此为未应至而至。即冬月严寒倍常,是为至而太过,所感乃真伤寒耳(眉批:可知伤寒亦时气之一耳,与温病原非一种)。设温煖倍常,是为至而不及,所感伤寒多合病、并病耳,即冬温也。假令夏月,时多风雨,炎威少息,为至而不及。时多亢旱,烁石流金,为至而太过。不及亦病,太过亦病,一时霍乱吐泻、疟痢咳嗽等项,不过因暑温而已。又若春秋俱行夏令,天地暴烈,人感受之,内外大?,舌胎口裂、腹脇胀满、头痛身痛,状类伤寒而实非伤寒,状类温病而实非温病,此即诸家所谓风温、暑温、湿温、秋温是也(按:此四证,乃时行之气所发,与温病根源不同。而怫?自内达外,与温病证治相同。馀每以温病十五方,时其轻重而施之屡效。盖能涤天地疵疠之气,即能化四时不节之气。古人云「方贵明其所以然」者,即此也),与冬温差近(按:冬温,即伤寒合病、并病也。先解表而后攻裏,以外束风寒故也。与四证不同,须明辩之)。凡此四时不节之时气病,即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病,所感终不离其本源。正叔和《序例》所云云者是也,于杂气所中之温病终何与焉?误以温病为时气病者,又宁不涣然冰释哉(眉批:将一切时气病说得明白坦亮,与温病毫无干涉,令人目开心明)? |
春温,夏暑,秋凉,冬寒,这是四时之气交替运行之次序,即使是「非其时有其气」,亦属于天地之常气,而杂气与此气并非同一类。杂气,非温非暑,非凉非寒,是天地之间另有一种疵疠旱潦之毒气,多发生在战争飢荒之年,但丰年岁亦有。在不同地方及四季不同时间上杂气有盛衰之不同,这就是温病之来由。王叔和《伤寒例》说:「春应温而反大寒,夏应暑而反大凉,秋应凉而反大?,冬应寒而反大温,非其时有其气。一岁之中,长幼之病多相似者,此则时行之气也」(旁批:杨慄山说:我读《伤寒绪论》「冬月温气乘虚入裏,遂成合病」,我领悟到冬温与风温、暑温、湿温、秋温以及疟疾、痢疾、咳嗽、呕吐、霍乱等病,都是时行之气所致之病,这正如王叔和所说。但杂气并非同一种类,冬温等病与温病有什么关系呢)。看到如此之说法,嘴裏说的是「时气」,心裏却将之当作「温病」,由此之后天下谈论温病都是以此为准。因而失去了对温病实质之理解,同时亦失去了对时气病实质之理解。总之,这是由于人们不知道温病是由疵疠旱潦之杂气所引致的,抑或不知道时行之气,是天气应热时而反冷,天气应冷时而反热,虽然当中有所变化,但其所发之病,又怎能够在出乎四时本气之外(眉批:伤寒病、温病、时气病,以前之方书常常混而为一,从此有了明确之区分,就能避免人们犯错,这是后人对前人尚未达到领域之突破)?假如春分之后,天气应温暖,偶然因风雨交集,不能温暖而天气反寒冷,所发之病,轻者为感冒,重者为伤寒。但是,春天寒冷之气,终究不似隆冬严寒之气具有杀疠之性,所以处方用药就有轻重之分,这是应来之气尚未来到所致之病。如果秋分之后,适逢风雨较多,强烈之寒气先到,所发病,大约与春天寒冷所致之病相似。而深秋之寒冷,亦不似隆冬严寒之气那么重,这是不应来之气反而先到。即使冬月时严寒倍于往常,这是当来之气来得太过,感受后所得之病就是真正的伤寒病(眉批:可知伤寒病亦是时行病之一,与温病原本就非同一种类)。假如冬时温暖倍于往常,这是当来之气来而有所不足,所发之伤寒病就较多合病、并病,即为冬温病。假如夏日裏风雨较多,天气沒有那么炎热,这亦是应来之气来而有所不足。如果夏时久旱不雨,天气酷热,这是当来之气来得太过。气不及会病,气太过亦会病。突然患上霍乱吐泻、疟疾、痢疾、咳嗽等病,不过是因为夏暑过热而已。又如果春秋之时都象夏天一样热,人感受天地暴烈之气,内外大热,以致口舌干裂、腹胁胀满、头痛身痛,病状类似伤寒病而实非伤寒病,类似温病而实非温病,此即医家们所说之风温、暑温、湿温、秋温(按:这四证是由时行之气所引发,与温病在根源上就不同。但其郁热自内而外发,因此与温病之证治方法相同。我屡屡会根据病情轻重而施用治疗温病之十五种方剂,获效良多。因为这些方能够涤除天地疵疠之气,即能化解四季不节之气。古人说「用方治病贵在明白其原理」,即是指这一点),与冬温差不多(按:冬温,即伤寒病之合病、并病。因为风寒外束,治疗时应先解表,后攻裏。与此四证不同,需要明确区分)。凡是这些四时不节所致之时气病,就是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之六气病,所感之邪气始终不能脱离其本源,这就是王叔和《伤寒例》中所表述之意思,与中于杂气所引发之温病有什么关系呢?误以为温病为时气病的人,现在难道不完全明白了吗(眉批:将所有时行之气所致之病都说得明明白白,与温病毫无关系,使人完全明白)? |
|
|
按:《内经》云「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」,谓春必病?也,非温病也。霜降后雨水前,风送寒来,寒随风入,伤寒即冬之时气也。又云「春伤于风,夏生飱泄」,即春之时气也。「夏伤于暑,秋必痎疟」,即夏之时气也。「秋伤于湿(湿,土也。土生金则燥),冬生咳嗽」,即秋之时气也(眉批:何等平易,何等切当,岂无春夏秋冬受伤当时即发者乎?不可执泥伤非藏于肌肤可知。)。知此便知温病非时气病,乃天地之杂气病也,后人多为叔和所误。 |
按:《内经》说「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」,是说春天必然病发热,而不是得温病。霜降之后雨水之前,风送寒来,寒随风入,伤于寒即是感受冬天之时气。又说「春伤于风,夏生飱泄」,即是春天之时气。「夏伤于暑,秋必痎疟」,即是夏天之时气。「秋伤于湿(湿,即湿土,土生金则燥),冬生咳嗽」,即是秋天之时气(眉批:表述非常直接和准确,难道春夏秋冬受邪,当时即发病的情况不存在吗?由此可知不可固执地认为邪气一定会藏于肌肤)。知道了这些,便知道温病并非时气所致之病,乃是天地之杂气所致之病,后人大多数是被王叔和之说所误。 |
|
|
又按:喻氏谓仲景独伤寒一门立法,乃四序主病之大纲也。春夏秋三时虽不同,其外感则一,自可取伤寒之方错综用之。此亦臆断,非确论也。所伤风暑湿燥,飱泄、疟痢、咳嗽,亦能杀人,何必定以冬寒为大纲,于三时不立法乎?至于包含万有,百病千方,不能出其范围,自是別具只眼(眉批:说得定)。 |
又按:喻嘉言认为仲景单独为冬伤于病立法,这是因为此乃四时气所伤之病之大纲。春夏秋三时之气虽然不同,但都属于外感病,自然可以取用治伤寒病之方交错运用。这亦是其个人之主观判断,而非正确之观点。因风、暑、湿、燥所伤而引发之飱泄、疟痢、咳嗽,亦都能伤害人,何必一定要以冬伤于寒为大纲,而不针对其他三时进行立法呢?至于喻氏认为《伤寒论》一书包罗万象,百病千方都不能出于其范围,这是有独到之见解(眉批:说得对)。 |
|
|
又按:春伤风,夏伤暑,秋伤湿,冬伤寒,是人感节气之变,虚损家多为所伤也。随感随病者固多,过时而病或亦有之。若中严寒杀厉之气,即至壮之人亦必病,难言过时发矣。诸家註释「四伤」,皆推求太过。但只平易说去,则经㫖自明,而无穿凿之患。 |
又按:春伤于风,夏伤于暑,秋伤于湿,冬伤于寒,是人感受四时气之变化,平素虚损之人容易为其所伤。受邪之后随即发病之人固然多,但亦有过了时节而发病之人。如果感受了严寒杀厉之气,即使是非常强壮之人亦必然会生病,很难说只有过了时节才发病。诸家在註释「四气所伤」之病时,皆是想得太多。只要用浅显易懂之文字去解释,经书之主旨自然明白,就不会有穿凿附会之过失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日月星辰,天之有象可观。水火土石,地之有形可求。昆虫草木,动植之物可见。寒暑风湿,四时之气往来可觉。至于山岚瘴气,岭南毒雾,兵㓙旱潦熏蒸,咸得地之浊气,犹或可察。而唯天地之杂气,种种不一,亦犹天之有日月星辰,地之有水火土石,气交之有寒暑风湿,动植之有昆虫草木也。昆虫有龙蛇勐兽,草木有桂附芭豆,星辰有罗计荧惑,土石有雄硫硇信。万物各有善恶,杂气亦各有优劣也。第无声无形,不覩不闻。其来也无时,其着也无方。感则一时不觉,久则蓄而能通。衆人有触之者,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。或时衆人发颐,或时衆人头面浮肿,俗名「大头温」是也。或时衆人咽痛声哑,或时衆人颈筋胀大,俗名「虾蟆温」是也。或时衆人吐泻腹痛,或时衆人斑疹疔瘇,或时衆人呕血暴下,俗名「搅膓温」、「瓜瓤温」是也。或时衆人瘿核红肿,俗名「疙瘩温」是也。或时衆人痿癖足重,俗名「软脚温」是也。大抵病偏于一方,延门合户,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藏府,某经络,专发为某病,故衆人之病相同,不关人之强弱,血气之盛衰。又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(眉批:情理宛然),是知气之所来无时也。或发于城市,或发于村落,他处安然无有,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。虽有多寡轻重不同,其实无处不有(眉批:温病本杂气,在六气外,来无时,着无方。此论发千古未发之奇,启后人无穷之智。业医者大宜留心)。如瓜瓤温、疙瘩温,缓者三二日死,急者朝发夕死,在诸温中为最重者。幸而几百年来罕有之病,不可以常时并论也。至于肿头发颐、喉痹咽肿、项强反张、流火丹毒、目赤斑疹、腹痛呕泻、头痛身痛、骨痿筋搐、登高弃衣、谵语狂叫不识人之类,其时村市中偶有一二人患此。考其证,甚合某年某处衆人所患之病,纤悉皆同,治法无二。此即当年之杂气,但目今所钟不厚,所患者稀少耳。此又不可以衆人无有,断为非杂气也。况杂气为病最多,然举世皆误认为六气(眉批:杂气为病甚于六气,以补河间《原病式》所未及)。假如误认为风者,如大麻风、鹤膝风、歷节风、老幼中风、痛风、厉风、癎风之类,概作风治,未尝一騐。实非风也,亦杂气之一耳。误认为火者,如疔疮发背、痈疳毒气流注、目赤瘴翳,以及斑疹之类,概作火治,未尝一騐。实非火也,亦杂气之一耳。误认为暑者,如疟痢吐泻、霍乱转筋、暴注腹痛,以及昏迷闷乱之类,概作暑治,未尝一騐。实非暑也,亦杂气之一耳。至误认为湿燥寒病,可以类推。又有一切无名暴病,顷刻即亡,无因而生,无识乡愚认为鬼祟,并皆杂气所成。从古未闻者,何也?盖因来而不知,着而不觉,人唯向风寒暑湿燥火所见之气求之,而不索之于无声无形,不覩不闻之中。推察既已错认病源,处方未免误投药饵。《大易》所谓「或系之牛,行人之得,邑人之灾」 也。刘河间作《原病式》,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气,殊不知杂气为病更有甚于六气者。盖六气有限,现在可测。杂气无穷,茫然不可测也。专务六气,不言杂气,乌能包括天下之病欤?(此吴又可杂气论也,馀订正之,更其名曰「温病是杂气非六气辩」)。 |
日月星辰,在天上有星象可以被观察。水火土石,在地上有物之形状可以被求证。昆虫草木,是动植物可以被看见的。寒暑风湿,是四季气候可以被感知的。至于山岚瘴气,岭南毒雾,以及战争、干旱和洪水所带来的灾难,都源自于地之浊气,尚且可以被察觉到。只有天地间之杂气,种种不一,就像天空有日月星辰,地面有水火土石,气候交替之中有寒暑风湿,动植物之中有昆虫草木。昆虫有龙蛇勐兽,草木有桂枝、附子、巴豆,星辰中有罗睺、计都、荧星、惑星,土石有雄磺、硫磺、朱砂、信石。万物各有善恶,杂气也各有优劣。只是杂气是无声无形,看不见听不到。其来无定时,其着落亦无定向。感受到杂气时当时不觉,日久之后则能积聚并传递至他处。当人们接触到它时,会随着杂气之不同而患上各种疾病。或者众人头面肿胀,或头面浮肿,俗称「大头温」。或者众人咽痛声哑,或者众人颈筋肿大,俗称「蛤蟆温」。或者众人呕吐腹痛,或者众人斑疹脓肿,或者众人呕血和腹泻,俗称「搅肠温」、「瓜瓤温」。或者众人颈侧肿块红肿,俗称「疙瘩温」。或者众人肢体萎缩,下肢沉重,俗称「软脚温」。一般来说,疾病偏向某一方向,挨家挨户受到影响,当时正好有某种离气专门侵犯某个脏腑、经络,专门引发为某种疾病,因此众人患病相同,这与个人之强弱、血气之盛衰并无关系。又不可以某年某时来划定其发病(眉批:于临床上合情合理),这样就知道杂气之来并无定时。或者发生在城市,或者发生在村落,其他地方则安然无事,这样就知道杂气之着落亦无定向。虽然发病之人有多少不同,其病情有轻重不同,但其实杂气是无处不在(眉批:温病源于杂气,是在六气之外,来无定时,着落无定向。这种理论千古未有,启发了后人无尽之智慧。从事医学之人对此应该格外留意)。例如,瓜瓤温、疙瘩温,发作缓慢之人,两三天即死亡,而急性发作者,早上发病,当晚即死,是各种温病中最严重的一类。所幸的是,此乃百年难遇之病,不能与常见之温病相提并论。至于头面肿胀、喉痹咽肿、项强而角弓反张、流火丹毒、目赤斑疹、腹痛呕吐泄泻、头痛身痛、骨痿筋抽、登高脱衣、谵语狂叫而不识人等证候,有时在村落或城市偶尔见有一两人患有此病。对其证候加以仔细考察,则与某年某地众人所患之病非常相符,细节都一样,治疗方法也沒有区別。这就是当年杂气所致之病,只是目前并未广为传播,所以患者稀少罢了。这又不可以因为不是众人都发病,就断定它不是杂气。况且杂气致病最为常见,然而举世都误将其认作六气所致之病(眉註:杂气为病比六气为病更为严重,这是补充刘河间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所未及之处)。如果误将杂气认为是风邪,例如大麻风、鹤膝风、歷节风、老幼中风、痛风、厉风、癎风等,一概以风论治,沒见过有一例被治好的。因为这实际上并非风病,亦只是杂气之一。如果误将杂气认为是火邪,例如疔疮发背、痈疽、毒气流注、目赤瘴翳,以及斑疹等,一概以火论治,沒见过有一例被治好的。因为这实际上并非火病,亦只是杂气之一。如果误将杂气认为是暑邪,例如疟疾、痢疾、呕吐泻利、霍乱转筋、暴注腹痛,以及昏迷闷乱等,一概以暑论治,沒见过有一例被治好的。因为这实际上并非暑病,亦只是杂气之一。至于误将杂气认为是湿燥寒病等,都可以类推。还有一切无名之急病,瞬间即死亡,并不知其发病之因,无知之乡人都认为是鬼祟,实际上都是由杂气所致。从古至今从未曾听闻,为什么呢?因为杂气来时不能被觉察,袭人之后亦难被发觉,人们只有从风寒暑湿燥火等可见之气求之,而不从无声无形、无法被察觉之杂气中寻找病原。既然在认识疾病过程中错认了病源,所处之方药也必然错误。《易经‧无妄卦》说:「无妄之灾,或者是因为牛被拴住,行人获得了这头牛,但却为邑中人带来了灾祸。」刘河间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认为百病都源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气,哪裏知道杂气所致之病比六气病更为严重。六气是有限的,根据现在可以预测未来。而杂气则无穷无尽,茫然无法预测。只专注于六气而不言杂气,怎么能涵盖天下所有疾病呢?(这是吴又可之杂气论,我对其进行修订,更名为「温病是杂气非六气辩」)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夫所谓「杂气」,虽曰天地之气,实由方土之气也。盖其气从地而起,有是气即有是病,譬如天地生万物,亦由方土之产也。但植物藉雨露而滋生,动物赖饮食 |
所谓「杂气」,虽说是天地之气,实际上是源自不同地方之气。因为杂气是从地面而起,有了这种气就会有了这种病,就像天地生万物,亦是由不同地方之气而生。只不过植物通过雨露而生长,动物靠食物颐养。先有了这种气,然后才有了这些生物。推而广之,有了无限之气,就有了无限之物(眉批:杂气之危害甚于六气,通过观察事物就可以知道人了,人们不过是习以为常而不察。至于其深奥之理论,就像平时说话一样,又非学识者能说出来)。只是阴阳五行之气不免会有生剋制化,所以万物各有宜忌。适宜者就会增益,不适宜者者就应该减损,所谓「损」就是制约之意。所以万物各有制约,如猫制鼠,鼠制象之类。既然知道以物制物,就应该知道以气制物之理。所谓「以气制物」,如螃蟹受到雾气则死,枣树受到雾气则枯等等。这是有形之气对动植物都有所制约。至于无形之气遍中于动物,则形成猪温,羊温,牛温、马温,那裏只会导致人之温病呢?但是猪病而羊不病,牛病而马不病,人病而禽兽不病,探究其所伤不同之因,只是其气不同而已。正因为其气不同,所以称之为「杂气」。物由气化而生,气乃物之变。物即是气,气即是物。知道气可以制物,就知道物亦可以制气。物可以制气的例子就是药物,如蜒蚰解蜈蚣毒,穿山甲治疗蚁毒所致之瘻等。这是因为受到物之气而为病,所以或许可以推测用某物之气来制约某物之气。至于受到无形之杂气所致之病,就不知道用何物能够制约杂气。正因为不知道何物能够制约杂气,所以只能勉强使用汗法、吐法、下法、和法这四种方法来医治。唉!如果真的知道用某物来制约杂气,一种病只需用一种药,又何必麻烦使用四种方法,而且要考虑君臣佐使、药物之加减,分两轻重之劳苦,以及用何方合适与否,见效与否,担心会否影响生命之生死等!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凶年温病盛行,所患者衆,最能传染,人皆惊恐,呼为「瘟疫」。盖杂气所锺者盛也,以故鸡温死鸡,猪温死猪,牛马温死牛马,推之于人,何独不然?所以兵荒饥馑之岁,民多夭札,物皆疵疠,大抵春夏之交为甚。盖温暑湿热之气交结互蒸,人在其中,无隙可避。病者当之,魄汗淋漓,一人病气,足充一室。况于连床并榻,沿门閤境,共酿之气。益以出户尸虫,载道腐墐,燔柴掩席,委壑投崖。种种恶秽,上溷空明清凈之气,下败水上污浊之气。人受之者,亲上亲下,病从其类(眉批:《经》云「清邪中上焦,浊邪中下焦」,即「亲上亲下,病从其类」二语可征矣。所谓读书有得者是也,岂伤寒外感表证所可同哉)。如世所称「大头温」,头面腮颐,肿如瓜瓠者是也(加味凉膈散)。所称「虾蟆温」,喉痹失音,颈筋胀大者是也(增损双解散)。所称「瓜瓤温」,胸高脇起,呕汁如血者是也(加味凉膈散)。所称「疙瘩温」,徧身红肿,发块如瘤者是也(增损双解散,玉枢丹外敷)。所称「绞肠温」,腹鸣干呕,水泄不通者是也(增损双解散)。所称「软脚温」,便清泻白,足重难移者是也(增损双解散、升降散皆可。眉批:升降散,温病主方也,此六证可参用)。其邪热伏郁三焦,由血分发出气分,虽有表证,实无表邪,与正伤寒外感之表证全无干涉,人自不察耳。必分温病与瘟疫为两病,真属不通。盖丰年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,且不传染,并不知为温病,以致徃徃误事,盖杂气所锺者微也。馀自辛未歷騐,今三十余年,伤寒仅四人,温病不胜屈指。乐岁之脉证,与?荒盛行之年缐悉无异。至用药取效,毫无差別。轻则清之,重则泻之,各行所利,未有不中病者。若认为伤寒时气,误投发散,为祸不浅;误投温补,更成痼疾。所以陈良佐曰:「凡发表温中之药,一概禁用。」此尤不可不辩也。 |
凶年时,温病流行,患者众多,传染性最强,人们都感到惊恐,称之为「瘟疫」。杂气所影响的范围广泛,所以鸡温就使鸡死,猪温就使猪死,牛马温就使牛马死,推之于人,为什么会不一样呢?所以在兵荒饥饿之年,人们夭折的情况就多,众物皆受疵疠之气影响,大抵以春夏之际尤为严重。因为温暑潮湿和炎热之气候相互交结,人处其中,无处可避。发生疾病时,汗出流离,一人之病气充满于室内。更何况同床共枕,同一门户,共同酝酿同一病气。加上尸体置于门外而腐烂,用柴火烧或只用席子掩盖尸体,或将尸体投入沟壑,种种恶臭污秽,在上则扰动清明之气,在下则败坏水中浑浊之气。人若受之,上者亲上,下者亲下,所患疾病都类同(眉批:《经》文说「清邪中上焦,浊邪中下焦」,即「亲上亲下,病从其类」这两句话可以反映出来。这就是所谓读书而有心得,怎么可以与伤寒外感表证之说相比)。譬如,现在所称之「大头温」,即头面部、腮颏肿胀如瓜瓠(用加味凉膈散)。所称之「虾蟆温」,即喉痹而失音,颈筋肿胀(用增损双解散)。所称之「瓜瓤温」,即胸胁隆起,呕吐之物带血(用加味凉膈散)。所称之「疙瘩温」,即全身红肿,出现肿块如瘤(用增损双解散,外敷玉枢丹)。所称之「绞肠温」,即腹鸣干呕,水样泄泻但不畅(用增损双解散)。所称之「软脚温」,即大便清稀色白,下肢沉重难行(用增损双解散和升降散皆可。眉批:升降散是治疗温病之主方,以上六种证候可灵活使用)。邪热伏郁于三焦,由血分外达于气分,虽然有表证,但实际上沒有表邪,与正伤寒病治外感表证完全沒关系,医家们只是沒有认识到这一点。坚持将温病与瘟疫区分开来,实在于理不通。在丰收富裕之年,民间所患之病人只有少数,而且沒有传染性,都不知道这是温病,往往以致误诊误治,因为杂气所伤之人只属少数。我自辛未年开始行医至今三十余年,遇到患伤寒病之人仅有四人,温病则数不胜数。富裕之年岁,病者之脉证与灾荒凶年之病完全沒有区別。至于用药取效,亦毫无差別。轻者则清之,重者则泻之,根据不同情况来用药,沒有不取得良好效果的。如果将其作为伤寒时气之病,误用辛温发散,则为祸不浅;如果误用温补,更会导致顽疾。所以陈良佐说:「凡是发表温中之药,一概禁用。」这一点尤其不能不加以说明。 |
| 原文 |
|
翻译 |
|
《伤寒论》曰:「凡治温病,可剌五十九穴。」只言「温病」,未有所谓「瘟疫」也。后人省「氵」,加「疒」为「瘟」,即「温」字也。省「彳」,加「疒」为疫,即「役」字也。又如病证之「证」,后人省「登」,加「正」为「証」。后又省「言」,加「疒」为「症」,即「证」字也。古文并无「瘟」字、「疫」字、「証」字、「症」字,皆后人之变易耳。不可因变易其文,遂以「温病」、「瘟疫」为两病。《序例》以「冬之伏寒,至春变为温病,至夏变为暑病」。又以「冬时有非节之煖,名为瘟疫」。「春分后,秋分前,天有暴寒者,名为寒疫病?」云云(眉批:自叔和「伏寒」、「暴寒」之论定,而后世诸家循沿旧闻,喻氏谓「一盲引衆盲,相将入火炕」,甚是之谓欤)。其后《活人书》以「冬伤于寒,因暑而发为?病,若三月至夏为晚发伤寒」。又以「非其时有其气,责邪在四时专令之藏1,名为春温、夏温、秋温、冬温」。云岐子2以伤寒汗下过经不愈,如见太阳证,头痛,发?,恶寒,名为「太阳温病」;见阳明证,目痛,鼻干,不眠,名为「阳明温病」;见少阳证,胸脇痛,寒?呕而口苦,名为「少阳温病」;见三阴证,名为「三阴温病」云云。又以发斑,名为「温毒」。汪氏以春之温病有三种,「有冬伤于寒,至春变为温病者;有温病未已,再遇温气而为瘟疫者;有重感温气,相杂而为温毒者。」又以「不因冬伤于寒,不因更遇温气,只于春时感春温之气而病,可名春温」云云。诸如此类,叙温者络绎不绝,议温者纷纭各异,其凭空附会,重出叠见,不唯胶柱鼓瑟,且又罪及无辜。果尔,则当异证异脉,不然,何以知受病之原不一也。设使脉证大相悬殊,又当另立方论治法。然则脉证何异,方论治法又何立哉?所谓「枝节愈繁而意愈乱」,学者不免有多歧之惑矣(眉批:见得真,说得透,放得倒)。夫温者?之始,?者温之终,故夏曰「?病」,而春曰「温病」也。因其恶厉,故名为「疫疠」。终有得汗而解者,故又名为「汗病」。俗名为「瘟疫」者,盖「疫」者「役」也,如徭役之役,以其延门合户,衆人均等之谓也,非两病也。此外,又有「风温」、「暑温」、「湿温」、「秋温」、「冬温」之名,明明皆四序不节,所谓「非其时有其气」,乃风、火、暑、湿、燥、寒之邪,天地之常气为病也,与温病何相干涉?总缘人不知天地间,另为一种疵疠旱潦之杂气而为温病,俗名「杂疾」是也(眉批:此句凡三见,非重出也。正是大声连呼,唤醒世人处)。诸家愈说愈凿,无所不至矣。噫!毫釐千里之谬,「一唱百和」之失,千古同悲。馀故不辞固陋,详为论辩,以就正于知物君子。《温疫论》曰:「温病本于杂气,四时皆有,春夏较多,常年不断,不比㓙年之盛且甚耳。」《序例》、《活人》、汪氏,悉属支离,正如头上安头,「伏寒」、「异气」,原非温病根源。云岐子则又指鹿为马,并不知伤寒、温病原是两途,未有始伤寒而终温病者。若是温病,自内达外,何有传经?若果传经,自是伤寒由外之内,而非温病也。又曰:温病初起,杂气?郁腠理,亦发?恶寒,状类伤寒,后但?而不恶寒也。其脉不浮不沉,中按洪长滑数,甚则沉伏。昼夜发?,日晡益甚。虽有发?恶寒,头痛身痛等证,而怫?在裏,浮越于外,不可认为伤寒表证,輙用麻黄、葛根之类强发其汗。其邪原不在经,汗之反增狂燥,?亦不减,此温病之所以异于伤寒也。 |
《伤寒论》说:「凡治温病,可刺五十九穴。」只说「温病」,沒有所谓的「瘟疫」。后人将「氵」省略,加上「疒」而成为「瘟」,其实就是「温」字。省略了「彳」,加上「疒」而成为「疫」,其实就是「役」字。又譬如病证之「证」,后人省略了「登」,加上「正」而成为「証」,后来又省略了「言」,加上「疒」而成为「症」,其实就是「证」字。古文中并沒有「瘟」字、「疫」字、「証」字、「症」字,这些都是后人改变了文字而来。不可以因为改变了文字,就将「温病」、「瘟疫」视为两种疾病。《序例》认为「冬之伏寒,至春变为温病,至夏变为暑病」。又认为「冬时有非节之暖,名为瘟疫」。「春分后,秋分前,天有暴寒者,名为寒疫病热」等等(眉批:自王叔和提出「伏寒」、「暴寒」之后,后世医家沿袭旧闻,所以喻嘉言称「这是一个盲人引导众盲人,互相走入火坑」,情况真的就是如此)。其后《类证活人书》又提到「冬伤于寒,因暑气而发为热病,若三月至夏季才发病者,称为晚发伤寒」。又说「非其时而有其气,应该于四时当令之脏有关,分別称之为春温、夏温、秋温、冬温」。张璧则认为伤寒病汗下之后而过经不愈,出现太阳病之头痛、发热、恶寒等证,称为「太阳温病」;有阳明病之目痛、鼻干、失眠等证,称之「阳明温病」;有少阳病之胸胁痛、寒热往来、呕吐而口苦等证,称为「少阳温病」;有三阴病之证,则称为「三阴温病」等等。又将发斑者,称为「温毒」。汪氏提到春季之温病有三种,「一种是冬季受寒邪所伤,到了春季变为温病;一种是温病未愈,又遇到温邪而发展为瘟疫;一种是重复感受温邪,相杂而为温毒。」又提到「不因为冬季受寒邪所伤,亦不因为又遇到温邪,只在春季感受春温之气而发病,可以称为春温」等等。诸如此类,描述温病者络绎不绝,讨论温病者亦各种各样,经常是凭空附会,重复其说,这不仅仅是胶柱鼓瑟,而且会使无辜之人遭殃。如果真是这样,其脉证应该不同,否则如何知道其受病之原是不一样的呢?即使脉证候有较大差异,也应当另立方论和治法。如果是这样,脉证有何不同,方论治法又怎么确立呢?所谓「枝节愈繁而意愈乱」,学者难免有多歧亡羊之困惑(眉批:看得真,说得透,放得倒)。温是热之起始,热是温之结果,因此在夏季称为「热病」,在春季称为「温病」。由于其病兇险,所以被称为「疫疠」。最终可以透过出汗而解,所以也被称为「汗病」。世俗称之为「瘟疫」,因为「疫」有「役」之意,就像徭役之「役」,因为其病会遍及全家,有众人染病均等之意,并非两种不同之病。此外,还有「风温」、「暑温」、「湿温」、「秋温」、「冬温」等名称,明明都是因为四季之气失和,所谓「非其时有其气」,即风、火、暑、湿、燥、寒等邪气,是天地之常气所致之病,与温病又有任何关系呢?总因人们不知道天地之间,另外有一种疵疠旱潦之杂气而引致温病,即俗称为「杂疾」(眉批:这句话出现过三次,并不是重复。正是大声疾呼,想唤醒世人)。医家们愈说愈似真实,无所不至。唉!毫釐之误,千里之谬,「一唱百和」之失,千古同悲。我所以不怕自己见识浅陋,对此加以详细论辩,想抛砖引玉而请教于真正有见识者。《温疫论》说:「温病本源于杂气,四季皆有,春夏较多,全年不断出现,只是不能与凶年多发或严重相比。」《伤寒例》、《类证活人书》、汪氏等看法都是散乱而不完整,就好比在头上面再放一个头,「伏寒」、「异气」并非温病之病源。而张璧则又指鹿为马,并不知道伤寒病和温病原本是两种不同之病,沒有开始是伤寒病而最成为温病的。如果是温病,是从内向散发展,那裏会有传经呢?如果确有传经之变,那就是伤寒病由外入裏,而不是温病。再说,温病初起时,杂气之热拂鬰腠理,也会类似于伤寒病而发热恶寒,之后就只有发热而不恶寒。其脉不浮不沉,中取洪长滑数,甚至脉沉伏。昼夜都发热,日晡之时更严重。虽然有发热、恶寒、头痛、身痛等证,但这是在裏拂郁之热浮越于外所致,不能将其认定为伤寒病之表证而用用麻黄汤、葛根汤之类强行发汗。因为病邪原本并非在经络中,发汗反而会增加狂躁与津枯,发热亦不减,这就是温病之所以与伤寒病不同。 |
|
|
按:又可《温疫论》以温病本于杂气,彻底澄清,看得与伤寒判若云泥,诸名公学不逮此,真足启后人无穷智慧。独惜泥于邪在膜原半表半裏,而创为「表证九传」3之说,前后不答,自相矛盾,未免白圭之玷。然不得因此而遂弃之也,馀多择而从之。 |
按:吴又可之《温疫论》指出温病源于杂气,观点清清楚楚,将温病与伤寒病区分开来,众多医家都达不到这一点,真是启发了后人无穷之智慧。遗憾的是,他坚持邪气停留在膜原之半表半裏,并创造了「表证九传」之说,前后不一而自相矛盾,难免有白圭之玷。但亦不能因此而完全抛弃他的学说,我就从中选择并认同其不少观点。 |
|
|
1 四时专令之脏:指五脏应四时,而四时之气各异,如春温、夏热、秋凉、冬寒,故其后有春温、夏温、秋温、冬温之说。 |
|
|
|
2 云岐子:即金元医家张壁,着有《伤寒保命集》、《云岐子脉诀》等书。 |
|
|
|
3 表证九传:吴又可《瘟疫论·统论疫有九传治法》虽说将温疫病之传变归纳为九种,但其文却有十种,即:但表而不裏、但裏而不表、表而再表,裏而再裏、表裏分传、表裏分传再分传、表胜于裏、裏胜于表、先表后裏、先裏后表。 |
| 原文 |
|
翻译 |
|
凡人大劳大慾,及大病久病,或老人枯稿,气血两虚,阴阳并竭,名曰「四损」。真气不足者,气不足以息,言不足以听,或欲言而不能,感邪虽重,反无胀满痞塞之证。真血不足者,通身痿黄,两唇刮白,素或吐血、衂血、便血,或崩漏产后失血过多,感邪虽重,面目反沒赤色。真阳不足者,或厥逆,或下利,肢体畏寒,口鼻气冷,感邪虽重,反无燥渴谵妄之状。真阴不足者,肌肤甲错,五液1干枯,感邪虽重,应汗不汗,应厥不厥。辩之不明,伤寒误汗,温病误下,以致津液愈为枯涸,邪气滞濇,不能转输也。凡遇此等,不可以常法正治,当从其损而调之。调之不愈者,稍以常法正治之。正治不愈者,损之至也。一损、二损,尚可救援,三损、四损,神工亦无施矣。 |
凡是人过度劳作纵慾、及大病久病,或者年老枯藁,气血两虚,阴阳并竭者,谓之「四损」。真气不足者,气弱不足以息,言语不足以听,或者欲言而不能言,虽然感受到严重之邪,反而沒有胀满痞满等证。真血不足者,则全身萎黄,两唇苍白,或平时就有吐血、鼻衄、便血病史,或者崩漏、产后失血过多等,虽然感受严重之邪,反而沒有面色红赤。真阳不足者,或厥逆、或下利、肢体畏寒,口鼻冷气等,虽然感受到严重之邪,却沒有口燥、口渴、谵妄等证。真阴不足者,则肌皮肤甲错,五液干枯,虽然感受到严重之邪,应该出汗反而无汗,应该寒厥反而不厥。如果对上述状况不能明确辨別,治疗伤寒病时误汗,治疗温病时误下,都会使体内津液更加干枯,邪气滞涩而难以透散。凡是遇到这些情况,就不能按照常规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,而应根据其具体虚损之情况进行调治。调治后仍然无效,才可以稍微用常规方法加以治疗。如果常规之的治疗仍然无效,那就反映虚损非常严重了。一损、二损,尚有救治之机会,三损、四损,神医亦无法挽救了。 |
|
|
按:病有纯虚纯实,非清则补,有何乘除?设有既虚且实者,清补间用,当详孰先孰后,从少从多,可缓可急,纔见医家本领。馀丙子在亳,生员张琴斯正,年过六旬,素多郁结,有吐血证,岁三五犯,不以为事也。四月间,忽而发?头痛身痛,不恶寒而作渴,乃温病也。至第二日,吐血倍常,更觉眩晕,大?神昏,手足战掉,咽喉不利,饮食不进。病家、医家但见吐血,便以发?眩晕神昏为阴虚,头痛身痛战掉为血虚,非大补不可救。不察未吐血前已有发?作渴,头痛身痛之证也。馀曰旧病因温病发,血脱为虚,邪?为实,是虚中有实证也,不可纯补。馀用炙甘草汤去桂枝,加归、芍、熟地黄、五味、犀、丹、殭蚕、蝉蜕,二服血已不吐,诸证减去七分。举家归功于参,均欲速进,馀禁之竟不能止。又进一服,遂觉烦?顿作,胸腹否闷,徧体不舒,终夜不寐,时作谵语。馀曰:诸证皆减,初补之功也。此乃本气空虚,以实填虚,不与邪搏。所余三分之?,乃实邪也,再补则以实填实,邪气转炽,故变证蜂起。遂与升降散作丸服,微利之而愈。后因劳復,以参柴三白汤治之而愈。后又食復,以栀子厚朴汤加神麯六钱而愈。引而伸之,触类而长之,可以应无穷之变矣。 |
按:病有纯虚或纯实,不是清热就是补虚,又有何变化呢?假如有既虚且实者,那么清热和补虚之间,需考虑先后顺序,或少或多及或缓或急等,这才能显现医者之本领。丙子年间,我在亳州遇到一位秀才名叫张琴,年过六十,素来多七情郁结,有吐血病史,每年发作三到五次,自己并不觉得是件大事。在四月份,突然发热、头痛、身痛、不恶寒但口渴,这是温病。到第二天,吐血加倍,更觉得晕眩、高热、神昏、手足颤抖、咽喉不利、不能饮食。家人和医者只看到吐血,就以为发热、眩晕、神昏为阴虚,头痛、身痛、颤抖为血虚,必须大补才能治疗。却沒有注意到在未吐血之前已经有发热、口渴、头痛、身痛之证。我说旧病是因温病而復发,血脱是虚证,邪热是实证,是虚中有实之证,不能单纯补益。我用炙甘草汤去桂枝,加入当归、白芍、熟地黄、五味子、犀角、朱砂、僵蚕和蝉蜕,服用两剂后病者已停止吐血,各种证候都减轻了七成。家人们都认为功劳都在于人参,都希望加重人参之用量。我阻止都阻止不了。又服了一剂,烦躁、发热骤起、胸腹痞闷、全身不舒服、整夜无法入睡,还时不时谵语。我说:各种证候都减轻了,这是起初补益之功效。这是因为当时正气空虚,用补益药,不会充实邪气。所余下之三分热,就是实邪,再补益就会充实邪气,邪气因而转盛,所以各种变证都出来了。于是我就将升降散制成丸剂给病人服用,稍微通便后病才好转。后来因为过劳復发,我再用参柴三白汤治疗而愈。之后又因为饮食不当而復发,我用栀子厚朴汤加神曲六钱而愈。由此引申开来,触类旁通,则可以应对疾病无穷之变化。 |
|
|
1 五液: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:「五脏化液:心为汗,肺为涕,肝为泪,脾为涎,肾为唾。是为五液。」 |
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凡伤寒足太阳膀胱经,从头顶贯腰嵴,故头项强,发?恶寒。然风寒常相因,寒则伤荣,头痛恶寒,脉浮紧,无汗,麻黄汤主之,开发腠理以散寒,得汗而愈。风则伤卫,头痛恶风,脉浮缓,有汗,桂枝汤主之,充塞腠理以散风,汗止而愈。若风寒并受,荣卫俱伤,大青龙汤主之。此三方者,冬月天寒腠密,非辛温不能发散,故宜用也。若夫春夏之温病,其杂气从口鼻而入,伏鬰中焦,流布上下,一发则炎?炽盛,表裏枯涸,其阴气不荣,断不能汗,亦不可汗,宜以辛凉苦寒清泻为妙。轻则清之,神解、清化、芳香之类;重则下之,增损双解、加味凉膈、升降之类,消息治之。伤寒汗后?不退,此阴阳交而魂魄离也,证亦危矣。其势稍缓者,宜更汗之。若反剧烦躁者,必有夹食夹痰,或兼有宿病,当寻其源而治之。若发?烦躁,小便不利,为?入膀胱之本,五苓散主之。温病清后?不退,脉洪滑数,或沉伏,表裏皆实,谵妄狂越,此?在三焦也,加味六一顺气汤、解毒承气汤大下之。伤寒传至阳明,则身?目痛,鼻干不得卧,葛根汤。表裏俱盛,口渴引饮,脉洪大,白虎汤,此在经之?也。传至少阳,为半表半裏之经,往来寒?,胁满口苦而呕,默默不欲食,小柴胡汤加减和之。过此不解,则入阳明之府。表证悉罢,名为「传裏」,潮?谵语,唇焦舌燥,大便秘,脉沉实长洪,如痞满燥实四证皆具,大承气汤主之。但见痞满实三证,邪在中焦,调胃承气汤,不用枳朴,恐伤上焦之气。但见痞满二证,邪在上焦,不用芒硝,恐伤下焦之血也。小腹急,大便黑,小便自利,喜忘如狂,蓄血也,桃仁承气汤代抵当汤丸。湿?发黄,但头汗出,茵陈蒿汤。伤寒下后?不退,胸中坚满不消,脉尚数实者,此为下未尽,或下后一二日復发?喘满者,并可用大柴胡汤,或六一顺气汤復下之。若下后仍不解,宜详虚实论治。如脉虚人弱,发?口干舌燥,不可更下,小柴胡汤、参胡三白汤和之。温病下后厥不回,?仍盛而不退者,危证也。如脉虚人弱,不可更下,黄连解毒汤、玉女煎清之。不能不下,黄龙汤主之。若停积已尽,邪?愈盛,脉微气微,法无可生,至此下之死,不下亦死,用大復甦饮,清补兼施,宣散蓄?,脉气渐復,或有得生者。《医贯》以六味地黄丸料,大剂煎饮,以滋真阴,此亦有理。若伤寒腹满而嗌干,则知病在太阴也;口燥咽干而渴,则知病在少阴也;烦满囊缩而厥,则知病在厥阴也。邪到三阴,脉多见沉,倘沉而有力,此从三阳传于三阴,?证也。外虽有厥逆,自利欲寝,舌卷囊缩等证,正所云「阳极发厥」,止该清之下之,自是桂枝加大黄、承气、六一一派(眉批:六一者,六一顺气汤也。加殭蚕、蝉蜕、黄连,即加味六一顺气汤也)。若本是阳证,因汗下太过,阳气已脱,遂转为阴证。夫邪在三阳,其虚未甚,胃气尚能与邪搏而为实?之证。邪到三阴,久而生变,其虚之甚也,气血津液俱亡,不能胜其邪之伤,因之下陷,而裏寒之证作矣。此?变为寒之至理。脉必沉而无力,证见四肢厥逆,心悸惕瞤,腹痛吐利,畏寒战慄,引衣蜷卧,急宜温之补之。阳虚者附子、四逆,阴虚者理阴、补阴。伤寒多有此证治,温病无阴证,?变为寒,百不一出,此辨温病与伤寒六经证治异治之要诀也(眉批:伤寒温病治法各別,层叠不乱,足见精密,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耳)。盖伤寒之邪,风寒外感,始中太阳者十八九。温病之邪,直行中道,初起阳明者十八九。信乎!治疗之宜早,而发表、清裏之宜谛当也。倘审之不谛,而误治之,即成坏病矣。 |
足太阳膀胱经从头顶贯腰嵴,因此凡伤寒足太阳膀胱经发病,会出现头项强痛、发热恶寒。然而,风邪与寒邪通常同时出现,寒则伤营,因而头痛、恶寒、脉浮紧而无汗,用麻黄汤主治,开发腠理以散寒,汗出则愈。风则伤卫,因而头痛、恶风、脉浮缓而汗出,用桂枝汤主治,充盈腠理以散风,汗出则愈。如果同时受风寒而营卫都受伤,则用大青龙汤主治。冬天寒冷而腠理紧闭,必须用此三方之辛温以发散,所以应该用。至于春夏之温病,杂气通过口鼻而入,郁积于中焦,布散全身,一发作就炎热炽盛,表裏津液干枯,病者阴气损伤,一定沒有汗,也不能发汗,当以辛凉苦寒清泻之法为上策。病轻者可以清热,用清解散、清化汤这类芳香类方剂;病重者则需要攻下,用增损双解散、加味凉膈散这类升降气机之方剂,根据证候而加减运用。伤寒病汗出后发热不退,属于阴阳交而魂魄离散,亦属于危重病证。其病势稍缓者,可以再次发汗。如果病势反而加剧,出现烦躁,必然是夹食积或夹痰饮,或者同时伴有以前之疾病,要找到其根源进行治疗。如果发热、烦躁、小便不利,是热邪入于太阳之本膀胱,用五苓散主治。而温病用清解后热不退,脉洪滑数,或者沉伏,邪气充斥表裏,谵妄狂越,为热在三焦,用加味六一顺气汤、解毒承气汤大下之。伤寒传至阳明经,则身热、目痛、鼻干而不得卧,用葛根汤。如果表裏邪气俱盛,口渴引饮、脉洪大,用白虎汤,这是热邪在阳明经。邪气传至少阳,这是半表半裏之经,则寒热往来、胁肋满、口苦而呕吐、默默不欲食,用小柴胡汤加减而和之。邪气过经不解,则入阳明之腑。表证完全消失,称为「传裏」,潮热、谵语、唇干舌燥、大便秘结、脉沉实长洪。如果「痞满燥实」四证齐全,用大承气汤主治。当只出现「痞满实」三证,邪气在中焦,用调胃承气汤而不用枳实和厚朴,以免伤害上焦之气。只是见到「痞满」二证,邪气在上焦,不用芒硝,以免伤害下焦之血。如果小腹急、大便黑、小便自利、喜忘、如狂等,这是有蓄血,用桃仁承气汤代替抵当汤或抵当丸。湿热发黄而但头部出者,用茵陈蒿汤。伤寒病攻下后热不退,胸中胀满,脉仍然数实者,这是攻下后邪气未尽,或者攻下后一两天又有发热而喘满,都可以用大柴胡汤或六一顺气汤再次攻下。如果攻下后仍然无效,则应仔细辨別虚实进行治疗。如果脉虚而人弱,发热、口干舌燥,则不宜再次攻下,用小柴胡汤、参胡三白汤和之。温病攻下后,仍手足寒厥,而发热仍盛而不退,属于危重证。对于脉虚人弱而不宜再次攻下者,用黄连解毒汤、玉女煎进行清解。不得不要攻下时,用黄龙汤主治。如果停滞积聚之邪已尽,而邪热愈盛,脉微气弱,应该无法使之回生,此时攻下则死,不攻下亦死,用大復苏饮清热与补益同时进行,宣散其蓄热,脉气能逐渐恢復者,或许还有生存希望。《医贯》用六味地黄丸原方大剂量煎煮服用,以滋养真阴,这也是有道理。伤寒病,如果腹满而嗌干,则知病在太阴经;口干咽干而渴,则知病在少阴经;腹中烦满、阴囊紧缩而四肢厥冷,则知病在厥阴经。邪气侵入三阴,多见脉沉,如果沉又有力,这是邪气从三阳传至三阴,属于热证。儘管外证有四逆、下利、欲寐、舌卷、囊缩等,这就是所谓的「阳极发厥」,只需要清热或攻下,用桂枝加大黄汤、承气汤、六一汤等(眉批:六一汤,就是指六一顺气汤,再加入殭蚕、蝉蜕、黄连等药物,就是加味六一顺气汤)。如果原本是阳证,但因发汗、攻下太过而导致阳气散失,就会转为阴证。当邪气尚在三阳时,其虚弱尚未严重,胃气仍能与邪气抗争,则为实热之证。当邪气到达三阴,久而生变,虚弱程度就会加深,气血津液俱亡,无法抵御邪气之伤害,邪气因而内陷而出现裏寒证候。这是热证化而为寒必然之道理。脉象必然沉而无力,证见四肢寒冷、心悸动惕、腹痛吐利、畏寒战慄、引衣踡卧等,此时急需温养补益。阳虚者用附子汤、四逆汤,阴虚者用理阴煎、补阴益气煎。伤寒病中多有此类证治,而温病无阴证,由热证变为寒证之情况极为少见,此乃区分温病与伤寒病六经证治之不同的要诀(眉批:伤寒病和温病之治疗方法各有不同,层次清晰而不混乱,足见其精密,然而临床运用之妙则在于医生是否用心)伤寒病是由于外的风寒之邪,其始发之病十有八九是太阳病。温病之邪直犯中焦,初病时十有八九是阳明病。确实是这样的啊!都应该尽早治疗,但一定要分清是发表还是清裏。如果对此不能准确分辨识而误治,就会导致坏病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「坏病」者,非本来「坏病」,医坏之也。谓伤寒不当汗而汗,不当下而下,或汗下太早,或汗下太迟,或汗下无力不及于病,或汗下过度虚其正气。如误汗则有亡阳衂血,斑黄谵语,惊惕眩冒;误下则有烦躁呕泻,结胸痞气,下厥上竭等证是也。《伤寒论》曰:「太阳病,已发汗,若吐,若下,若温针,仍不解者,此为坏病,桂枝不中与也。观其脉证,知犯何逆,随证治之。」又曰:「若已发汗、吐下、温针,谵语,柴胡证罢,此为坏病。观其脉证,知犯何逆,以法治之。」前一段桂枝不中与,谓表证已罢,邪已传变。后一段柴胡证罢,谓半表半裏之证已罢,邪入更深。仲景「随证治之」一语,语活而义广。以视王、韩诸公专主温补者,为尽善也。若温病一坏,势虽烈于伤寒,果随证治之,亦有得生者,但不可卤莽灭裂耳。又温病拂?内鬰,断无传经之理。伤寒则以七日为一候,其有二候三候不解者,病邪多在三阳经留恋。仲景《伤寒论》原本《内经‧?论》一篇,并无「过经」、「再经」明文,唯有「七日太阳病衰,头痛少愈」,「八日阳明病衰,身?少歇」,「九日少阳病衰,耳聋微闻」,「十日太阴病衰,腹减如故」,「十一日少阴病衰,渴止舌润而嚏」,「十二日厥阴病衰,囊纵少腹微下,大气皆去,病人之精神顿爽矣」。玩本文六「衰」字,语意最妙。盖谓初感之邪,至七日及十余日尚未尽衰,则可或汗吐下错误,以致邪气愈炽,则可自当依坏病例治之。岂有厥阴交尽于裏,再出而传太阳之事哉?试质之高明。 |
所谓「坏病」,并非原本就是「坏病」,只是由医生治疗不当所导致。指的是伤寒病时不应该发汗却发汗,不应该攻下却攻下,或者发汗下太早或太迟,或者汗下不足而病不除,或者汗下太过而伤及正气。譬如误汗可以导致阳气亡阳、衄血、黄斑、谵语、惊惕、眩晕;误下则可以导致烦躁、呕吐、泻泄、结胸、痞气、上下虚竭等证。《伤寒论》说:「太阳病,已发汗,若吐,若下,若温针,仍不解者,此为坏病,桂枝不中与也。观其脉证,知犯何逆,随证治之。」又说:「若已发汗、吐下、温针,谵语,柴胡证罢,此为坏病。观其脉证,知犯何逆,以法治之。」前一段提到桂枝不能再用,指的是表证已罢,邪气已经传变。后一段提到「柴胡证罢」,指的是半表半裏证已罢,邪气进一步深入。仲景「随证治之」一语,语气灵活而含义广泛。看来王、韩等医者专注于温补,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。如果温病一旦出现「坏病」,儘管病势比伤寒病勐烈,但只要根据具体证候进行治疗,也有能被治好的,只是不能鲁莽地治疗。另外,温病的热邪郁闭,绝不会有传经之理。伤寒病则以七天为一个阶段,如果 两个或三个阶段都沒有好转,邪气多停留在三阳经络。仲景《伤寒论》原本是按照《内经‧热论》这一篇,并沒有「过经」、「再经」之文,只有「七日太阳病衰,头痛少愈」,「八日阳明病衰,身?少歇」,「九日少阳病衰,耳聋微闻」,「十日太阴病衰,腹减如故」,「十一日少阴病衰,渴止舌润而嚏」,「十二日厥阴病衰,囊纵少腹微下,大气皆去,病人之精神顿爽矣」。仔细品味文中六个「衰」字,其语意最妙。这是说初感之邪,到了七天或十几天仍未完全衰退,此时就可能由于错误地发汗、涌吐或攻下,而导致邪气更加炽盛,就可以根据「坏病」之证治来处理。怎么会有邪气于厥阴经行经尽后,又再次传至太阳经的道理呢?请问高明之士,你怎么看呢?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表裏俱病,阴阳并传,谓之「两感」,乃邪亢极之证。冬月正伤寒,病两感者亦少。一部《伤寒论》仅见麻黄附子细辛汤一证,有太阳之发?,故用麻黄;有少阴之脉沉,故用附子、细辛。发表温裏并用,此长沙正伤寒太阳少阴之两感治法也(《内经》曰:「一日头痛发?恶寒,口干而渴,太阳与少阴俱病」)。即此而推,阳明与太阴两感,自当以阳明太阴二经之药合而治之。(《内经》曰:「二日身?目痛,鼻干不眠,腹满不食,阳明与太阴俱病」)。少阳与厥阴两感,自当以少阳厥阴二经之药合而治之(《内经》曰:「三日耳聋脇痛,寒?而呕,烦满囊缩而厥,水浆不入,少阳与厥阴俱病」)。病有外内,药有标本,斟酌合法,未必如《内经》所云必死也。惟温病两感最多。盖伤寒两感,外感之两感也。温病两感,内伤之两感也(旁批:慄山曰:「馀读景岳书得钱氏论,而悟伤寒温病两感,一感于外,一伤于内,确切不易也。」眉批:伤寒两感属外感,温病两感属内伤,此论精切的当,发从来所未有)。伤寒得于常气,受病在经络,如前注《内经》所云云者是也。温病得于杂气,受病在藏府。钱氏曰:「邪气先溃于藏,继伤于府,纵情肆欲,即少阴与太阳两感。劳倦竭力,饮食不调,即太阴与阳明两感。七情不慎,疲筋败血,即厥阴与少阳两感」(按:钱氏虽未说出温病,实温病确论也。从此分辩温病与伤寒异处,自了然矣。眉批:註解谛当)。此所以内之郁?为重,外感为轻,甚有无外感而内之郁?自发者,不知凡几。河间特制双解散、三黄石膏汤,为两解温病表裏?毒之神方,即以补长沙「凡治温病,可刺五十九穴」之泻法也。《缵论》谓「河间以伤寒为杂病,温病为大病,其见高出千古,深得长沙不传之秘」,知言哉。馀观张、刘二公用方,正以辩温病与伤寒两感异治之要诀也。祖长沙,继河间,以着书立说者,何啻汗牛充栋,未见有方论及此者。间或有之,亦挂一漏百,有头无尾。馀纠合前贤,广采众论,于散遗零星中凑集而畅发之,而分晰之,务使温病脉证不致混人伤寒病中,温病治法不致混人伤寒方中。后有识者,或不以馀言为谬云(眉批:扫除一切,省悟一切)。干隆乙亥、丙子、丁丑、戊寅,吾邑连岁饥馑,杂气遍野,温病甚行,馀推广河间用双解、三黄之意,因定升降散、神解散、清化汤、芳香饮、大小復甦饮、大小清凉散、加味凉膈散、加味六一顺气汤、增损大柴胡汤、增损普济消毒饮、解毒承气汤,并双解、三黄亦为增损,共合十五方。地龙汤亦要药也,出入损益,随手辄应。四年中全活甚众,有合河间心法,读《缵论》不禁击节称赏不置也(地龙汤,即蚯蚓捣烂,入新汲水,搅净浮油,饮清汁,治温病大?诸证)。 |
表裏俱病,阴阳并传,称为「两感」,是邪气极盛之病证。冬天之正伤寒,两感之病较少见。在《伤寒论》一书中,只提到了一种方证,即麻黄附子细辛汤证,有太阳病之表热,因此用麻黄;有少阴病之脉沉,所以用附子和细辛。此方发表温裏并用,正是仲景治疗正伤寒之太阳少阴两感之法,(《内经》说:「第一天头痛发热恶寒,口干而渴,是太阳和少阴同时受病」)。由此推之,阳明与太阴之两感,自然应该结合阳明和太阴之方药进行治疗(《内经》中说:「第二天身热,目痛,鼻干不眠,腹满不食,是阳明和太阴同时受病」)。少阳与厥阴之两感,自然应该结合少阳和厥阴之方药进行治疗(《内经》中说:「第三天耳聋胁痛,发热恶寒而呕吐,烦闷,阴囊紧缩而厥冷,水浆不入,是少阳和厥阴同时受病」)。疾病有外感和内伤之分,用药也有标本之別,根据具体情况斟酌适当的治疗方法,就不一定会出现象《内经》所说的「必死」。只是温病中两感最为常见。伤寒之两感是属于外感之两感,而温病之两感是则属于内伤之两感(旁批:杨慄山说:「我读到张景岳之书时,书中提到钱氏的论述,才领悟到伤寒和温病之两感,一种是外感,一种是内伤,这是非常确切而不会改变的。」眉批:伤寒之两感属于外感,温病之两感属于内伤,这个论点非常精确,以前的人从来沒有提出过)。伤寒是由常气所引发之疾病,病变在经络中,就像前面《内经》中所描述的那样。温病是由杂气所引发之疾病,病变在脏腑之间。钱氏说:「邪气首先犯脏,然后伤腑,若放纵情欲,就会导致少阴与太阳两感;若劳倦用力,饮食不调,就会导致太阴与阳明两感;若七情不慎,伤筋耗血就会导致厥阴与少阳两感」(按:钱氏虽然沒有提到温病,而对温病而言,这实际上是非常精确的。由此来区分温病与伤寒病的不同,自然非常清楚。眉批:此註极为恰当)。这就是为什么由内而发之郁热较重,而外感之证较轻,甚至沒有外感而完全是由在内之郁热自发之疾病,不知道有多少。刘河间特制之双解散、三黄石膏汤,是治疗温病表裏热毒之神方,就可以补充仲景「凡治温病,可刺五十九穴」的说法。《伤寒缵论》说「刘河间将伤寒病看作杂病,温病看为大病,其见解超越了千古,深得仲照不传之秘」,说得真好啊。我研究了张璐、刘完素两位医者的用方规律,正真是分辨温病和伤寒病之两感不同治疗之要诀。本于张仲景,继承刘完素而着书立说者,其数量之多,汗牛充栋,但其方论从来都沒有论及此事。偶尔有一些,也都是挂一漏百,有头无尾。我广泛汇集前贤各种说法,从零散的资料中汇集并加以发扬,务必使温病之脉证不至于混入伤寒病中,温病之治法不至于混入伤寒病方剂中。后来有能理解我的人,或许不会认为我所说的是错误的(眉批:扫除一切杂说,能使所有人省悟)。干隆乙亥、丙子、丁丑、戊寅年间,我居住的地方,年年饥馑,杂气遍野,温病盛行,我将刘河间之双解散、三黄散推而广之,因而创立了升降散、神解散、清化汤、芳香饮、大小復苏饮、大小清凉散、加味凉膈散、加味六一顺气汤、增损大柴胡汤、增损普济消毒饮、解毒承气汤,并将双解散、三黄石膏汤亦进行增损,共合十五方。地龙汤亦是很重要之方,根据情况加减,用起来总能得心应手。四年中救命无数,能与刘河间之心法相合,阅读《伤寒缵论》时令人不禁击节称赞而不愿放置一边(地龙汤,即将蚯蚓捣烂,加入新汲水,搅拌之后清除浮油,只饮用清汁,治疗温病大热等证)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凡伤寒合病,两经三经齐病,病之不传者也。并病者,先见一经病,一二日又加一经病,前证不罢,两经俱病也。若先见一经病,更变他证者,又为传经矣。夫三阳合病,必互相下利(眉批:《伤寒论》合病止三证)。如太阳与少阳合病,脉浮而弦,自下利者,黄芩汤。太阳与阳明合病,脉浮而长,自下利者,葛根汤。喘而胸满者,不可下,麻黄汤。若心下满,腹痛,宜下之,调胃承气汤。阳明与少阳合病,脉弦而长,必下利,其脉不负者,顺也,小柴胡汤加葛根、白芍。若脉不长而独弦,利不止,不食者,名曰负。负者,也,土败木贼则死也。若脉兼滑而数者,有宿食也,宜大承气汤,急从下夺,乃为解围之善着。若脉不滑数而迟弱,方虑上败垂亡,尚敢下之乎?宜小柴胡汤合痛泻要方,或可救之。太阳与阳明并病,太阳未罢,面色缘缘正赤,或烦躁者,桂枝麻黄各半汤。若太阳已罢,潮?,大便实,手足濈濈汗出,此内实也,调胃承气汤。若脉弦而长,口苦,胸满,壮?者,小柴胡汤加葛根、白芍。若脉弦洪大,?盛舌燥,口渴饮水者,小柴胡汤合白虎。若太阳与少阳并病,头项强痛,眩冒,如结胸状,心下痞硬,当刺大椎第一间、肺腧、肝腧(刺大椎,泻手足三阳经也。刺肺腧,使肺气下行,而膀胱之气化出也。刺肝腧,所以泻胆邪也)。不善刺者,宜小柴胡汤加栝蒌、黄连、枳实、桔梗,或柴苓汤,慎不可下。若下之,便成结胸、痞气、下利不止等证(眉批:《伤寒论》并病止二证)。凡三阳合病,身重腹满,难以转侧,口不仁,面垢,谵语,遗尿,自汗者,白虎汤。若一发汗,则津液内伤,谵语益甚。若一下之,则阳邪内陷,手足厥冷,?不得越,故额上汗出也。惟有白虎汤主解?而不碍表裏,在所宜用耳。大抵治法,某经同病,必以某经之药合而治之,如人参败毒散、沖和汤,乃三阳经药。麻黄汤、桂枝汤、大青龙汤,乃太阳经药。葛根汤、白虎汤,乃阳明经药。小柴胡汤,乃少阳经药。凡太阳经未罢,当先解表。若表已解,而内不瘥,大满大实,方可用承气等汤攻之也(按:今伤寒多合病并病,未见单经挨次相传者,亦未见表证悉罢止存裏证者。况多温病,乌能依经如式,而方治相符乎)。《绪论》曰:「伤寒合病,多由冬月过温,少阴不藏,温气乘虚入裏,然后更感寒邪,闭郁于外,寒?错杂,遂至合病。其邪内攻,必自下利。不下利即上呕,邪气之充斥奔迫,从可识矣。必先解表,后清裏。其伤寒合病,仲景自有桂枝加葛根汤、葛根加半夏汤、葛根汤、麻黄汤等治法,观仲景治例可见矣。」馀谓冬月温气乘虚入裏,虽曰「非其时有其气」,到底是天地常气,所以伤寒合病名曰「冬温」。即此而推,所谓风温、暑温、湿温、秋温,亦皆时气也,与温病杂气所得根源不同。 |
凡是伤寒合病,同时出现两经或三经病证,这种情况不是疾病之传变。所谓「并病」,先见某一经之病证,一两天后又出现另一经之病证,先前之证候仍在,两经都病了。如果先见某一经之病证,后来变成其他经之病证,那就是传经了。三阳合病必然会出现下利(眉批:《伤寒论》中合病只有三条条文),比如太阳与少阳合病,脉浮而弦,自下利者,用黄芩汤。太阳与阳明合病,脉浮而长,自下利者,用葛根汤。喘而胸满者,不可下,用麻黄汤。如果心下满、腹痛,宜攻下,用调胃承气汤。阳明与少阳合病,脉弦而长,必下利,如果其脉搏不负者,为顺,用小柴胡汤加葛根、白芍。如果脉不长而弦,下利不止,不能食,这种情况叫做「负」,「负」,代表不顺,土气不足而木气乘土,这是死证。如果脉兼滑数,表示有宿食,用大承气汤,立刻通过攻下以除邪,就是化解危机之好方法。如果脉不滑数而迟弱,正要担心气血垂亡,还敢用攻下之法吗?应该用小柴胡汤合痛泻要方,或许还有救。太阳与阳明并病,太阳证尚未消失,面色通红,或烦躁,用桂枝麻黄各半汤。如果太阳证已消失,而见潮热,大便实,手足续持出汗者,这属于内实,用调胃承气汤。如果脉弦而长,口苦,胸闷,壮热者,用小柴胡汤加葛根、白芍。如果脉弦洪大,热盛而舌干,渴欲饮水者,用小柴胡汤合白虎汤。如果太阳与少阳并病,头颈强痛,眩晕,如结胸病之证,心下痞硬,应当刺大椎第一节、肺俞、肝俞(刺大椎,能泄手足三阳经气。刺肺俞,使肺气下行,而膀胱之气化则能出。刺肝俞,用以泄胆之邪气)。不擅长针刺之医者,可用小柴胡汤加栝蒌、黄连、枳实、桔梗,或者用柴苓汤,谨记不可用攻下法。如果误用攻下法,则会导致结胸、痞气、下利不止等证(眉批:《伤寒论》中并病只有二条条文)。凡是三阳合病,则身重,腹满,身体难以转侧,口中麻木,面垢,谵语,遗尿和自汗,用白虎汤。一但误用发汗,津液受损,则会加剧谵语。一但误用攻下,阳邪内陷,则会导致手足厥冷,热邪无法外越,故额上出汗。只有白虎汤能够清热而不阻碍表裏之气,此时最适合用白虎汤。从治法而言,某经之同病,必须使用该经之方药相合治疗。例如,人参败毒散、沖和汤是三阳经之方药,麻黄汤、桂枝汤和大青龙汤是太阳经之方药,葛根汤、白虎汤是阳明经之方药,小柴胡汤是少阳经之方药。凡太阳经证未罢,应首先解表。如果表证已解,裏证仍在,出现腹部大满大实,才可以使用承气等方进行攻下。(按:现在伤寒病多合病与并病,未见有循经依次相传者,也未见有表证完全消除而仅存裏证者。况且更多见的是温病,怎么会发生循经依次传变之模式而与用方治疗相一致的呢?)《伤寒绪论》中提到:「伤寒合病,大多由冬月过于温暖,少阴气不藏,温气乘虚入裏,然后再次感受寒邪,闭郁于外,寒热交杂,最终导致合病。邪气内攻必然下利,如果不下利就会出现呕吐。邪气之充斥而奔迫,由此就可以知道了。所以必须先解表,然后清裏。对于伤寒合病,仲景有桂枝加葛根汤、葛根加半夏汤、葛根汤和麻黄汤等治法,从仲景所列的各种治疗中可以看出来。」我认为冬月温邪乘虚入裏,虽然说是「非其时而有其气」,到底是天地之常气,所以伤寒合病称为「冬温」。由此作进一步推论,所谓风温、暑温、湿温、秋温,也都是时气所致,与温病是由杂气所致,其发病之根源是不同的。 |
|
|
按:伤寒,感冒风寒常气,自表传裏,故多循序而传,而合病并病为极少。温病因杂气怫?,自裏达表,或飢饱劳碌,或忧思气郁,触动其邪,故暴发竞起,而合病并病为极多。甚有全无所触,止是内鬰之?,久则自然蒸动。《绪论》之「邪气充斥奔迫」六字,可为伤寒合病并病传神,并可为温病传神。故温病但见太阳、少阳证,即可用增损大柴胡汤。但见三阳证,即可用加味凉膈散。伤寒见太阳少阳合病,必俟邪?渐次入裏,方可用黄芩汤。见三阳合病,必有身重,腹满,谵语,自汗,方可用白虎汤,又何论大柴胡、凉膈散乎?太阳阳明并病,在伤寒自是麻黄、葛根之类。盖伤寒但有表证,非汗不解也。在温病自是神解、升降、增损双解之类,不可发汗。裏气清而表气自透,汗自解矣。太阳少阳并病,在伤寒小柴胡汤加减治之,在温病增损大柴胡汤。此辩温病与伤寒,合病并病异治之要诀也。(眉批:此段议论开扩万古心胸,推倒一世豪杰,令长沙见之当亦无异说矣)。 |
按:伤寒病是感受风寒之常气,外邪从表传裏,通常是循三阳三阴经之顺序传变,而合病和并病的情况很少出现。温病是由杂气郁热所致,自裏外达于表。可能是由于饥饱劳碌,或者忧思气郁,触动邪气而突然发作,所以合病和并病就很常见。甚至有时完全沒有诱发因素,只是内郁之热,日久而自然蒸动。《伤寒绪论论》中提到「邪气充斥奔迫」六个字,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伤寒之合病和并病,也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温病之发病。因此,温病只要见到太阳、少阳证,就可以用增损大柴胡汤。只要见到三阳证,就可以用加味凉膈散。伤寒病中出现太阳少阳合病,必须等邪热逐渐入裏,才可以使用黄芩汤。出现三阳合病,必然有身重,腹满,谵语和自汗,才可以用白虎汤,又怎么会用到大柴胡汤和凉膈散呢?太阳阳明并病,在伤寒病中自然用麻黄汤、葛根汤等方,因为伤寒只要有表证,不发汗就不能解表。而在温病中,自然是用神解散、升降散、增损双解汤等方,不可发汗,裏热清而表气自然透达,自然汗出而解。太阳少阳并病,在伤寒病中用小柴胡汤加减进行治疗,而在温病中则用增损大柴胡汤。这就是辨温病和伤寒病中出现合病和并病时,在治疗上的关键所在。(眉批:这段论述打开了一直存于心中之疑虑,推翻了不少名家之见解,即使仲景看了之后亦不会不同意)。 |
| 原文 | 翻译 | |
|
「大头」者,天行疵疠之杂气,人感受之,壅遏上焦,直犯清道,发之为大头温也。世皆谓风寒闭塞而成,是不知病之来歷者也。若头巅脑后项下及耳后赤肿者,此邪毒内蕴,发越于太阳也。鼻頞两目,并额上面部,焮赤而肿者,此邪毒内蕴,发越于阳明也。耳上下前后,并头角赤肿者,此邪毒内蕴,发越于少阳也。其与喉痹项肿,颈筋胀大,俗名「蛤蟆温」,正《经》论所云「清邪中上焦」是也。如「绞肠温」吐泻湫痛,「软脚温」骨痿足重,正《经》论所云「浊邪中下焦」是也。如「瓜瓤温」胸高呕血,「疙瘩温」红肿发块,正《经》论所云「阴中于邪」是也。古方用白殭蚕(二两酒炒),全蝉蜕(一两),广姜黄(去皮三钱),川大黄(生,四两),为末,以冷黄酒一盅,蜜(五钱),调服三钱,六证并主之。能吐能下,或下后汗出,有升清降浊之义,因名「升降散」,较普济消毒饮为尤胜(外用马齿苋,入麦曲并醋少许,捣,敷肿硬处甚妙)。夫此六证,乃温病之中最重且凶者,正伤寒无此证候,故特揭出言之,其余大概相若。七十余条,俱从伤寒内辩而治之,正以明温病之所以异于伤寒也,正以明伤寒方之不可以治温病也。知此则不至误伤人命耳(眉批:引证确切,铁案不移,长沙亦应三肯其首。晋后名家林立,方书充栋,未见有发明温病至此者,妙在仍从《伤寒论》中看出,见得真,放得倒)。 |
「大头温」,是人感受天行疵疠之杂气后,邪气堵塞了上焦,直接侵犯了清阳之道,从而形成了大头温。世人都认为是风寒阻塞所致,是因为不了解此病之来歷。如果头顶、脑后、项下,以及耳后之红肿,这是邪毒内蕴发于太阳所致。鼻旁、两眼以及面部发红肿胀,这是邪毒内蕴发于阳明所致。耳朵上下前后以及头角红肿,这是邪毒内蕴发于少阳所致。而证见喉痹、颈部肿胀、颈筋膨大者,俗名「蛤蟆温」,正是《经》所说的「清邪中于上焦」。如果是「肠绞温」,则呕吐泄泻而腹中绞痛,「软脚温」则骨痿足重,正是《经》所说的「浊邪中于下焦」。如果是「瓜瓤温」,则胸满咳血,「疙瘩温」则红肿结块,正是《经》所说的「阴中于邪」。古方使用酒炒白殭蚕(二两),全蝉蜕(一两),去皮广姜黄(三钱),生川大黄(四两),研成末,以冷黄酒一盅,蜜(五钱),送服三钱,可用治此六种温病。此方能使涌吐,能使泄下,或者使泄利后汗出,具有升清降浊之作用,因此被称为「升降散」,比普济消毒饮更为有效(外用马齿苋,加入麦芽、神曲和少许醋,研碎,外敷于肿坚处非常有效)。温病中,此六种类型是最严重和兇险的,正伤寒并沒有这些情况,所以我特別提出来,其他情况大致相似。这七十多条,都是从伤寒病中分辨出来而加以治疗,目的是为了明确温病与伤寒病是不同的,也是为了说明伤寒方不能用来治疗温病。知道这一点,就不会误伤人命了(眉批:引证确切,铁证如山,即使仲景亦应同意此观点。自晋朝之后,名家林立,方书充栋,未见到有人将温病论述到这个程度,最妙之处在于这仍然是从《伤寒论》中看出来的,观察真切,言之合理)。 |
|
|
喻氏曰:「叔和每序伤寒,必插入异气,欲鸣己得也。及序异气,则借意《难经》,自作聪明,漫拟四温,疑鬼疑神,骎成妖妄。」世医每奉叔和序例如箴铭,一字不敢辩別,故有晋以后之谈温者,皆伪学也。慄山独取经论《平脉篇》一段,定为温病所从出之原,条分缕析,別显明微,辩得与伤寒各为一家,豪无矇混,不为叔和惑煽,直可追宗长沙矣(畏斋先生识)。 |
喻嘉言说:「王叔和《伤寒例》中每每必插入异气,意在显示自己的见识。写到异气时,便借用《难经》,自作聪明,无中生有地提出四种温病,疑神疑鬼,荒诞不经。」世医者每每将王叔和《伤寒例》之文视作箴言,不敢有丝毫辨別,所以晋朝以后提到温病者,都是伪学者。只有杨慄山单单取《平脉法》一段文字,确定了温病之根源,条分缕析,特別能明确细微之处,将温病与伤寒病各为一家分辨得清清楚楚,绝无混淆,不被王叔和之说迷惑,而是直接追溯至仲景之学术(畏斋先生明白了)。 |